“我的绝望与重生”
曾经,他为感染艾滋病迷惘、恐惧、无助,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如今,他走过了那段心理危机,勇敢面对着“携艾”的生活
记者金微采访整理 我叫刘九龙,男,出身在江西农村。初中没有毕业,我就到了珠三角打工。2005年,我开始发现自己有些不对劲——我身边的朋友都喜欢女孩,可我却喜欢男孩。可能是文化水平不高,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同性恋,后来在网上看了很多同性恋的介绍,我才慢慢接受自己就是同性恋这个现实。
“我本以为卖血才会得艾滋”
我只有两次性行为,后来因为身体上的某些反应,2007年春节我回了老家。在当地医院做了性病检查,医生在看了我的症状后,建议我去做HIV检测。
3月27号,我在老家的市疾控中心做了检查,4月2号收到了检测报告。那天我永远记得,愚人节刚过,我当时想:这个玩笑不会继续吧?但收到检测报告的那刻,我的心“咯噔”一下就下沉了。

我在医院时还谈笑风生,有位医生说:“小刘,别看你现在这么淡定,说不定一出门,你的眼泪就会掉下来。”他说对了,不用出门,在转身背对他的那刻,我就控制不住,眼泪不停地打转。那天雨下得好大,阴暗的天空跟我的生命似的,看不见前面的路。
我并不是怕死,是想到了父母,一闭眼,两个老人期盼的眼神,就在我脑海里,父亲70多岁,母亲60多岁。每年11月左右艾滋病人自述,他们就要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过年,什么时候结婚。我知道现在已经完不成这个任务了。过去,我觉得艾滋病离我很远,我以为只有卖血的人才可能得艾滋病,而且从不知道艾滋病会在我们这类人群中传播,包括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大学生,他也没有做安全措施。
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我分三次买了30片安眠药。卖药的店员问我是不是想自杀,他不敢多卖给我。说实话,我怕血,如果选择流血的方式,可能会殃及无辜,安眠药走了就走了,没有什么。当时我并没有想马上自杀,后来知道了艾滋病不会马上死,这些药我先攒着,如果我哪一天不行了,就把这些药给吃了。实不相瞒,这30片药我后来确实吃掉了,但被抢救回来了。
在确诊后,我一度非常绝望。在广州时,我怕到人多、明亮的地方,那时我觉得灯光很刺眼,感觉是在嘲笑你,迫于压力我回到了家乡。
在家呆了两个月,我不敢看母亲的眼神,觉得对不起她。劳累了一辈子,不就是希望唯一的儿子能成个家,抱个孙子,真是不敢看,看到那种描写亲情的电视剧,都会流眼泪。
“机会属于坚持自救的人”
后来,我在网上发现北京的治疗条件好。当时想:死活都要去北京。那时我还有侥幸心理,再做一次诊断。2007年9月,我带着打工赚的3000元钱,瞒着母亲说到北京治病。
在北京疾控中心,我最后做了次检查,奇迹并没有出现。10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第一句话就是:“请问你是刘九龙吗?”

感染后,我的心理防线很敏感,我问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他告诉我,他是疾控中心的一位志愿者,也是一位感染者。后来,他跟我讲起了他的故事,我突然觉得原来生命可以活成这样,是这位大哥让我有了继续生活的方向,抱歉的是,在这里我还不能说他的姓名。
之后,我经常参加一些感染者的交流活动,慢慢调整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北京佑安医院的一位老医生参加了一次感染者交流活动,我突然想到了母亲,那时她还不知道我感染了艾滋病,而且我一直隐瞒着同性恋的身份。我是家中独子,按照农村风俗,我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母亲在家四处帮我张罗婚事。可在农村,请媒人介绍对象是要钱的。
2008年11月,在离开一年多后,我回到了家乡。我告诉了母亲:“我不适合结婚了,这些钱你们留着好好生活吧。”
离开家时,母亲说:“儿啊,你不是说这种病,在平时是不会那么容易传染给别人吗?那你就好好的继续去生活,因为有你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妈妈才能感受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千万别想不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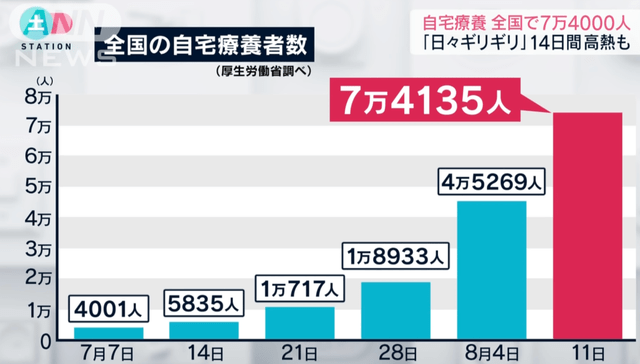
带着母亲的鼓励我来到北京,但是我只有初中文化,在北京很难找工作,曾经找过一份体力活,同性恋的身份暴露后立即被赶走。
但在北京这座城市,我收获更多的是感动,没钱的时候,有善良的人们帮我,无助的时候,他们鼓励我。特别是那位大哥,他曾经如此鼓励我:九龙,你一定要记住,上天更愿意把幸福的机会赐予坚持自救的人们。
我很感谢这座城市,当初,我从南方带着愧疚、自责、不甘、恐慌和懦弱来到这里!在这里,我经历了生与死的蜕变!学会了勇于去面对自己,珍惜生活,不放弃!
“我只希望有生之年做点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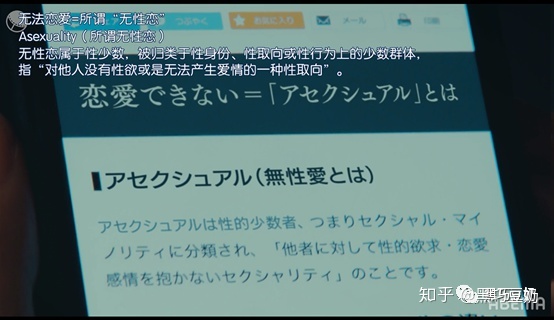
2009年9月,我再次准备回老家。在离开北京前,我想艾滋病所遭遇的歧视,大概会渗入到以后生活的每一天,人不会是永远幸运的,这是我对生活的感受。
回家后,跟家人和邻居讲解艾滋病毒的传染途径及特性时,我并没有遭到歧视。倒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他们的态度有些不一样。
我母亲年迈,加上农村收入不高,我想到乡政府领低保。当乡民政所所长看到我在申请原因上写着“艾滋病”时,所长直接把门关了起来,根本不让我进去。
后来,我了解到顾长卫导演正在筹备一部反映感染者真实生活的公益纪录片,并四处寻找感染者,我主动联系了剧组,剧组派赵亮导演到我家乡拍摄。记得赵亮在村里拍纪录片要到祠堂取景,村里人第一次看这种场面,纷纷聚过来艾滋病人自述,三言两语议论着。在他们拍摄时,村民们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婚姻,他们都敦促我尽快结婚,完成续香火的任务。我当时就调侃地说了句:我这辈子不会修那么长的路了(我父亲在家修了一辈子路),但我决不会去害人也不会骗人。
现在,我正在筹建江西关爱组织——“爱温暖家园”。我希望把北京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NGO模式带到这个中部省份,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人文关怀的工作,而江西省目前还没有这样感染者组织。
心理干预曾让我走出危机,我相信一些关爱组织是有用的,这里会为艾滋病毒感染者搭建一个相互交流,心灵休憩、停靠以及相互支持的家园。我希望能够和那些对生活绝望的感染者一起成长,也欢迎通过我的博客和我分享交流。
我不知我能做多少,我只希望有生之年做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