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不知道每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从前我们以为意外是天灾人祸,实际上一种致命的疾病也能将一个人彻底压垮。
艾滋病患者这个特殊群体一直都颇为社会所关注。
一名艾滋病患者曾经自述自己的经历,至今都不能确定自己是如何被感染的。

不知自己如何被感染
钱有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2020年时候是四十二岁。
他一直在工地上生活,平时就是扛钢筋、水泥,或者搬一些大理石,偶尔也做做油漆工。
和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农民工一样,他们干着又苦又累的体力活,以此来换取工资,养活一家老小。
2020年7月1日,那天烈日炎炎,钱有生照常出工。
他肩上扛着几块大理石,谁知走着走着脚崴了一下,手上一卸力,右边的肩膀就被砸伤了。
没有办法,钱有生只能先从工地回家,因为被砸伤了肩膀,上半身几乎动都动不了,穿衣吃饭都需要人照顾,他也不能麻烦工友。

到了家里他先是躺了几天,发现肩膀没有半点缓解,于是在妻子的催促之下,他决定去医院看看。
在医院,医生让钱有生做了X光片等详细检查,X光检查显示,他的右肩已经粉碎性骨折,情况非常严重。
医生对钱有生说,他现在已经不能再拖,必须要马上手术。
于是钱有生的手术时间被医生安排在了7月12日,钱有生先住进了医院,做一些术前的常规检查。
钱有生在医院紧张地等着,他主要还是怕手术的费用太高,家里条件不好,怕负担不起。
没过两天,主治医生独自一个人来到病房去找钱有生。
当时钱有生的妻子也在,妻子正在给钱有生削苹果吃,这几天钱有生因为要做检查抽了不少的血。

只见医生对妻子说,请她先出去一下,等会儿再进来。
妻子很疑惑,看了钱有生一眼,然后犹豫着出去了。
主治医生的反常行为让钱有生紧张了起来。
医生对他说,这里可能没有办法帮你做手术,你到北京或者天津去吧。
钱有生到现在还记得自己听到医生说这句话时的心情,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脑子里不停在想是不是自己做的检查,查出了什么不治之症,这个小地方治不了。
他赶忙追问医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能留在这做手术。
医生和他说,是因为艾滋病。
艾滋病。

听到这三个字,钱有生的脑子一片空白,他顿时连话都不知道说了,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结束和医生的谈话,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灵魂。
真的被自己猜中了,果然是不治之症!
医生说全省都没有医院可以给他做手术,只能去更大的城市。
万般无奈之下,钱有生出院了,在妻子的坚持下,他们前往北京看病,但是那些治疗骨科非常出名的医院根本挂不上号。
当时的钱有生已经感到生无可恋,他索性和妻子说不治了,回家养着吧,家里也没有那么多钱能让他奔波治疗了。

钱有生没有再治疗肩膀上的伤,所谓伤筋动骨一百天,养了很久,用了些土办法,钱有生的肩膀勉强好了,但是现在一高一低,每逢阴雨隐隐作痛,算是落下了残疾。
肩伤可以不治了,他自己能好,但是艾滋病却万万不行。
每当午夜梦回,钱有生脑子中就会不停地在想,自己究竟是怎么染上的艾滋病。
直到今天,他都无法确认确凿的感染途径,因为暴露在危险下的情况太多了。
艾滋病有三种传播途径,性接触、血液及血制品还有母婴传播。
钱有生的母亲很健康,也没有艾滋病,基本可以排除这种途径。
而其他两种途径,钱有生都有遭遇过。
钱有生说,自己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本事,所以一直都是干体力活。

长期重体力的劳动,让他的肩颈落下了顽疾,所以他会定期去进行理疗,缓解一下肩颈的压力。
说是理疗,其实还是乡下的土办法。
钱有生没什么钱,哪里会舍得去正规的理疗店或者医院进行调养,一般都是找一些小店。
但是小店的卫生安全情况可就没有人能够保证了。
钱有生说,他们当地有种理疗土办法,放血。
用一个和注射器很相似的东西,扎在不舒服的那一侧肩颈,然后把里面的“污血”吸出来,再放掉。
钱有生说,他去的时候有注意过,那些所谓的理疗师给他用的针并不是一次性的,只是进行了简简单单的消毒。
也就是说,如果针头上有其他人的体液,那么钱有生就是完全暴露在了感染的风险之下。
第二种途径的经历让钱有生感到有些难以启齿。
钱有生说,那是在工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他和一名中年男性被迫发生了性行为,而且是危险性行为,没有什么安全措施,他在过程中还出血了。

钱有生说,自己日日夜夜地想,想破头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得了病,但是等他去了解了艾滋病的相关知识之后,他知道,这两种经历很有可能就是导致他得病的原因。
“已经不重要了,是什么原因都不重要了,我这辈子已经毁了。”
现在的钱有生常年与药为伴,每天都要吃很多药,抗病毒和保护肝脏、肾脏。
艾滋病抗病毒的药物可以免费领取,但是其他的药需要钱有生自己买,因为艾滋病容易引起其他并发症,所以在控制病情的时候钱有生每个月要花费六百多元。
抗病毒的药是按月领取的,钱有生家中还有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儿女也都没有长大成人,他现在每个月都要领药,根本不可能外出打工。

没有办法打工,本来在家照顾家庭的妻子只能出去赚钱,一天能赚七十,勉强糊口。
钱有生在读高三的女儿学的还是美术专业,美术专业需要买画笔、颜料、画纸,都是不小的开销,但是钱有生坚持让孩子读下去。
女儿其实已经体会到了家里情况的窘迫,钱有生在家里养肩伤的那段时间,女儿不止一次和他说想要辍学,出去打工赚钱养家。
但每一次都被钱有生严厉地拒绝了,他告诉女儿,没有文凭在社会上过不下去。
看见女儿这个样子,钱有生更加不敢把自己得了艾滋病的事情告诉家里人,现在只有老婆知道他的情况。

谈到老婆,钱有生忍不住抹眼泪,他直呼自己对不起老婆。
他知道得病之后就想和老婆离婚,免得拖累她,但是老婆不肯,执意出去打工,养活这个家。
面对以后的路,钱有生感到很迷茫,因为那将是一个耗费金钱的无底洞。
检查花了快两千,每三个月要复查,每个月隔两周要去抽血……钱有生说到自己的检查项目,掰着指头算账,算着算着他便说不出话了。
艾滋病,这对一个本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像钱有生这样的艾滋病患者并不在少数,他们往往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染上的病毒,稀里糊涂地就成为了社会上的边缘人物。
因为艾滋病,患上了病症的他们有些医院不具备资格收治,只能去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就诊,背上了难以向家人启齿的沉重枷锁。
他们有的人妻离子散,有的人变得穷困潦倒,想要了却此生。

艾滋病人:挣扎与未来
在陕西西安,有位叫做刘言的艾滋病患者。
“给宋教授,一定要这个,”刘言竖起了大拇指,他哽咽地说,“让我们艾滋病患者,不让我们再拖延病情了。”
“拒诊两个字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刘言今年33岁,是一名艾滋病患者,17年3月的时候,他的屁股上发现了一个硬块。
“十二点的位置,有一个黄豆大小的疙瘩,不停地慢慢长大,然后由于擦屁股蹭破了,就开始流血。化验之后查出来是鳞状细胞癌。”

从17年3月份到2020年的5月,刘言一共被拒诊就此,皆因为他是一名艾滋病患者。

“因为很多人是住院以后查出来(艾滋病),我不想这样子,因为人要诚实。然后我就把我的病情一一介绍过了。”
刘言每次去医院求医的时候,都会和医生如实说出自己是艾滋病患者这件事,他不想让医护人员在为他检查身体的过程中暴露在感染的风险之下。
“他们也不算拒绝,就是这个科室退给那个科室,然后我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真的天都要塌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放弃,不想活了。”

在确诊了直肠癌之后,为了不拖累对象,刘言坚决地分了手。
2020年的3月,经过朋友的介绍,他来到了交大一附院,宋永春医生接诊了他,并成功做了手术。
“我心里还是很害怕,我是抱着最后耳朵希望来的,宋教授亲手给我做的检查,这个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宋教授)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宋医生表示,医生的天职就是给人看病,不管对方是否是艾滋病患者。
“手术呢,还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年轻人恢复非常快,他来我的门诊的时候,就和我说,大夫我得如实告诉你,我有艾滋病。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对于刘言这种情况,宋医生也呼吁,希望同行能够尽可能地帮助弱者。
“这个人首先是一个病人,虽然他有艾滋病,也不管他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他有没有权利接受医疗。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有权利的。”

钱有生当时治病的时候,就被医院拒绝了,而刘言也与他有着相同的遭遇,但刘言比他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医者仁心的宋医生。
从刘言和钱有生的经历,不难看出艾滋病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来有多么困难。
“我觉得能够活着真好,得了这种病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得了艾滋病之后,心里觉得快要完蛋了。”
这是艾滋病人知道自己病情之后的普遍心理。
俞阳,来自山东青岛,今年24岁,在2019年还在念大学的他因为发生同性性行为而感染了艾滋病,从此便踏上了漫长的治疗之路。
“确诊之后,我的心理压力很大。会想很多事情,家庭、同学之间还有个人身体方面。非常地后悔(发生同性性关系)。”
和钱有生一样,知道自己确诊之后,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考虑更多的是家庭,还有自己的社会关系,他在社会上今后要如何立足,会不会有异样的眼光。

“一次朋友聚会,算是酒后吐真言,我和朋友们说了这个病,活着也太累了。每天还得刻意隐瞒一些事情,用各种方法来掩饰自己的心情,然后直接就想跳楼。当时我就想直接攀着窗户往下跳,然后他们几个就拉着我。”
俞阳说,自己确诊之后,感觉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一个小秘密里,不想让任何外界的人知道这个秘密,在宿舍里没有人的时候,他会提前把药分装好,准备好一天的剂量。
因为先要完美地隐藏起来,所以舍友们在宿舍的时候,俞阳没有办法正常直接拿出来服药,他会把药放在裤子口袋里,然后去厕所服药。

俞阳不止一次地想过***,他常在网上看艾滋病患者发布的视频,在视频的下面会有很多人发表恶毒的评论,诸如:“你这样活着真是丢脸”、“你洁身不自好才会得这个病”……
每次看到这种评论,俞阳都觉得自己心如刀绞。
俞阳坦言,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受到了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的影响,让他重新拾起了活着的勇气。
如果按照他个人的想法、行为方式的话,就是破罐子破摔,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最开始俞阳认为这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病,后来才从青同那里知道,原来现在国家的政策也好,都有免费的药物,而且现在各种药物的治疗都是很有效的。

通过好好服药治疗,没有什么传染性。
深陷泥沼的俞阳在苦苦挣扎时知道了这样的消息,他觉得自己似乎还能看见未来。
俞阳没有让父母知道这件事,他坦言,他们会承受很大的打击,他自己本身承受的打击已经够大。
如果父母知道后万一有个好歹,自己会背负很大的罪恶感,所以他选择隐瞒。
钱有生、俞阳、还有千千万万个艾滋病患者,对他们来说,最难以承受的除了自己与病魔抗争之外,就是对别人袒露自己的病情,哪怕是最亲密的家人。
钱有生没有让儿女知道,俞阳没有让父母知道,他们这么做,是在保护家人,也是在保护自己。

关爱艾滋病患者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艾滋病患者都和钱有生一样,不知道自己怎么感染上的艾滋病。
他们对艾滋病的相关知识,是缺乏的,我们这个社会要做的,就是扩大艾滋病知识的宣传面,更要关爱艾滋病患者的心理健康。
国家、社会都在行动,而每个人其实都应该参与进来,只有深刻了解艾滋病知识,才能够避免越来越多的人重蹈覆辙。


你永远不知道每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从前我们以为意外是天灾人祸,实际上一种致命的疾病也能将一个人彻底压垮。
艾滋病患者这个特殊群体一直都颇为社会所关注。
一名艾滋病患者曾经自述自己的经历,至今都不能确定自己是如何被感染的。

不知自己如何被感染
钱有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2020年时候是四十二岁。
他一直在工地上生活,平时就是扛钢筋、水泥,或者搬一些大理石,偶尔也做做油漆工。
和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农民工一样,他们干着又苦又累的体力活,以此来换取工资,养活一家老小。
2020年7月1日,那天烈日炎炎,钱有生照常出工。
他肩上扛着几块大理石,谁知走着走着脚崴了一下,手上一卸力,右边的肩膀就被砸伤了。
没有办法,钱有生只能先从工地回家,因为被砸伤了肩膀,上半身几乎动都动不了,穿衣吃饭都需要人照顾,他也不能麻烦工友。

到了家里他先是躺了几天,发现肩膀没有半点缓解,于是在妻子的催促之下,他决定去医院看看。
在医院,医生让钱有生做了X光片等详细检查,X光检查显示,他的右肩已经粉碎性骨折,情况非常严重。
医生对钱有生说,他现在已经不能再拖,必须要马上手术。
于是钱有生的手术时间被医生安排在了7月12日,钱有生先住进了医院,做一些术前的常规检查。
钱有生在医院紧张地等着,他主要还是怕手术的费用太高,家里条件不好,怕负担不起。
没过两天,主治医生独自一个人来到病房去找钱有生。
当时钱有生的妻子也在,妻子正在给钱有生削苹果吃,这几天钱有生因为要做检查抽了不少的血。

只见医生对妻子说,请她先出去一下,等会儿再进来。
妻子很疑惑,看了钱有生一眼,然后犹豫着出去了。
主治医生的反常行为让钱有生紧张了起来。
医生对他说,这里可能没有办法帮你做手术,你到北京或者天津去吧。
钱有生到现在还记得自己听到医生说这句话时的心情,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脑子里不停在想是不是自己做的检查,查出了什么不治之症,这个小地方治不了。
他赶忙追问医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能留在这做手术。
医生和他说,是因为艾滋病。
艾滋病。

听到这三个字,钱有生的脑子一片空白,他顿时连话都不知道说了,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结束和医生的谈话,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灵魂。
真的被自己猜中了,果然是不治之症!
医生说全省都没有医院可以给他做手术,只能去更大的城市。
万般无奈之下,钱有生出院了,在妻子的坚持下,他们前往北京看病,但是那些治疗骨科非常出名的医院根本挂不上号。
当时的钱有生已经感到生无可恋,他索性和妻子说不治了,回家养着吧,家里也没有那么多钱能让他奔波治疗了。

钱有生没有再治疗肩膀上的伤,所谓伤筋动骨一百天,养了很久,用了些土办法,钱有生的肩膀勉强好了,但是现在一高一低,每逢阴雨隐隐作痛,算是落下了残疾。
肩伤可以不治了,他自己能好,但是艾滋病却万万不行。
每当午夜梦回,钱有生脑子中就会不停地在想,自己究竟是怎么染上的艾滋病。
直到今天,他都无法确认确凿的感染途径,因为暴露在危险下的情况太多了。
艾滋病有三种传播途径,性接触、血液及血制品还有母婴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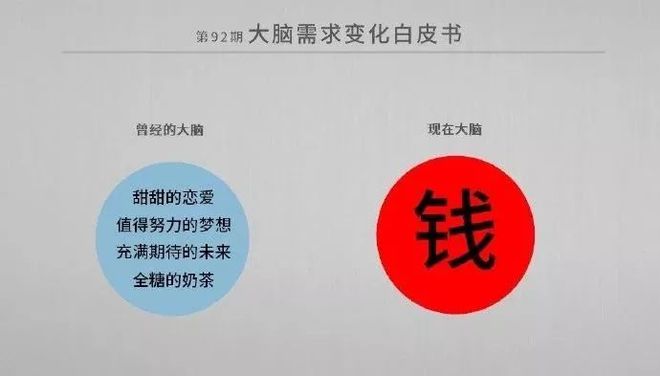
钱有生的母亲很健康,也没有艾滋病,基本可以排除这种途径。
而其他两种途径,钱有生都有遭遇过。
钱有生说,自己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本事,所以一直都是干体力活。

长期重体力的劳动,让他的肩颈落下了顽疾,所以他会定期去进行理疗,缓解一下肩颈的压力。
说是理疗,其实还是乡下的土办法。
钱有生没什么钱,哪里会舍得去正规的理疗店或者医院进行调养,一般都是找一些小店。
但是小店的卫生安全情况可就没有人能够保证了。
钱有生说,他们当地有种理疗土办法,放血。
用一个和注射器很相似的东西,扎在不舒服的那一侧肩颈,然后把里面的“污血”吸出来艾滋病人自述,再放掉。
钱有生说,他去的时候有注意过,那些所谓的理疗师给他用的针并不是一次性的,只是进行了简简单单的消毒。
也就是说,如果针头上有其他人的体液,那么钱有生就是完全暴露在了感染的风险之下。
第二种途径的经历让钱有生感到有些难以启齿。
钱有生说,那是在工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他和一名中年男性被迫发生了性行为,而且是危险性行为,没有什么安全措施,他在过程中还出血了。

钱有生说,自己日日夜夜地想,想破头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得了病,但是等他去了解了艾滋病的相关知识之后,他知道,这两种经历很有可能就是导致他得病的原因。
“已经不重要了,是什么原因都不重要了,我这辈子已经毁了。”
现在的钱有生常年与药为伴,每天都要吃很多药,抗病毒和保护肝脏、肾脏。
艾滋病抗病毒的药物可以免费领取,但是其他的药需要钱有生自己买,因为艾滋病容易引起其他并发症,所以在控制病情的时候钱有生每个月要花费六百多元。
抗病毒的药是按月领取的,钱有生家中还有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儿女也都没有长大成人,他现在每个月都要领药,根本不可能外出打工。

没有办法打工,本来在家照顾家庭的妻子只能出去赚钱,一天能赚七十,勉强糊口。
钱有生在读高三的女儿学的还是美术专业,美术专业需要买画笔、颜料、画纸,都是不小的开销,但是钱有生坚持让孩子读下去。
女儿其实已经体会到了家里情况的窘迫,钱有生在家里养肩伤的那段时间,女儿不止一次和他说想要辍学,出去打工赚钱养家。
但每一次都被钱有生严厉地拒绝了,他告诉女儿,没有文凭在社会上过不下去。
看见女儿这个样子,钱有生更加不敢把自己得了艾滋病的事情告诉家里人,现在只有老婆知道他的情况。

谈到老婆,钱有生忍不住抹眼泪,他直呼自己对不起老婆。
他知道得病之后就想和老婆离婚,免得拖累她,但是老婆不肯,执意出去打工,养活这个家。
面对以后的路,钱有生感到很迷茫,因为那将是一个耗费金钱的无底洞。
检查花了快两千,每三个月要复查,每个月隔两周要去抽血……钱有生说到自己的检查项目,掰着指头算账,算着算着他便说不出话了。
艾滋病,这对一个本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像钱有生这样的艾滋病患者并不在少数,他们往往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染上的病毒,稀里糊涂地就成为了社会上的边缘人物。
因为艾滋病,患上了病症的他们有些医院不具备资格收治,只能去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就诊,背上了难以向家人启齿的沉重枷锁。
他们有的人妻离子散,有的人变得穷困潦倒,想要了却此生。

艾滋病人:挣扎与未来
在陕西西安,有位叫做刘言的艾滋病患者。
“给宋教授,一定要这个,”刘言竖起了大拇指,他哽咽地说,“让我们艾滋病患者,不让我们再拖延病情了。”
“拒诊两个字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刘言今年33岁,是一名艾滋病患者,17年3月的时候,他的屁股上发现了一个硬块。
“十二点的位置,有一个黄豆大小的疙瘩,不停地慢慢长大,然后由于擦屁股蹭破了,就开始流血。化验之后查出来是鳞状细胞癌。”


从17年3月份到2020年的5月,刘言一共被拒诊就此,皆因为他是一名艾滋病患者。
“因为很多人是住院以后查出来(艾滋病),我不想这样子,因为人要诚实。然后我就把我的病情一一介绍过了。”
刘言每次去医院求医的时候,都会和医生如实说出自己是艾滋病患者这件事,他不想让医护人员在为他检查身体的过程中暴露在感染的风险之下。
“他们也不算拒绝,就是这个科室退给那个科室,然后我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真的天都要塌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放弃,不想活了。”

在确诊了直肠癌之后,为了不拖累对象,刘言坚决地分了手。
2020年的3月,经过朋友的介绍,他来到了交大一附院,宋永春医生接诊了他,并成功做了手术。
“我心里还是很害怕,我是抱着最后耳朵希望来的,宋教授亲手给我做的检查,这个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宋教授)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宋医生表示,医生的天职就是给人看病,不管对方是否是艾滋病患者。
“手术呢,还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年轻人恢复非常快,他来我的门诊的时候,就和我说,大夫我得如实告诉你,我有艾滋病。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对于刘言这种情况,宋医生也呼吁,希望同行能够尽可能地帮助弱者。
“这个人首先是一个病人,虽然他有艾滋病,也不管他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他有没有权利接受医疗。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有权利的。”

钱有生当时治病的时候,就被医院拒绝了,而刘言也与他有着相同的遭遇,但刘言比他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医者仁心的宋医生。
从刘言和钱有生的经历,不难看出艾滋病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来有多么困难。
“我觉得能够活着真好,得了这种病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得了艾滋病之后,心里觉得快要完蛋了。”
这是艾滋病人知道自己病情之后的普遍心理。
俞阳,来自山东青岛,今年24岁,在2019年还在念大学的他因为发生同性性行为而感染了艾滋病,从此便踏上了漫长的治疗之路。
“确诊之后,我的心理压力很大。会想很多事情艾滋病人自述,家庭、同学之间还有个人身体方面。非常地后悔(发生同性性关系)。”
和钱有生一样,知道自己确诊之后,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考虑更多的是家庭,还有自己的社会关系,他在社会上今后要如何立足,会不会有异样的眼光。

“一次朋友聚会,算是酒后吐真言,我和朋友们说了这个病,活着也太累了。每天还得刻意隐瞒一些事情,用各种方法来掩饰自己的心情,然后直接就想跳楼。当时我就想直接攀着窗户往下跳,然后他们几个就拉着我。”
俞阳说,自己确诊之后,感觉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一个小秘密里,不想让任何外界的人知道这个秘密,在宿舍里没有人的时候,他会提前把药分装好,准备好一天的剂量。
因为先要完美地隐藏起来,所以舍友们在宿舍的时候,俞阳没有办法正常直接拿出来服药,他会把药放在裤子口袋里,然后去厕所服药。

俞阳不止一次地想过***,他常在网上看艾滋病患者发布的视频,在视频的下面会有很多人发表恶毒的评论,诸如:“你这样活着真是丢脸”、“你洁身不自好才会得这个病”……
每次看到这种评论,俞阳都觉得自己心如刀绞。
俞阳坦言,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受到了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的影响,让他重新拾起了活着的勇气。
如果按照他个人的想法、行为方式的话,就是破罐子破摔,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最开始俞阳认为这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病,后来才从青同那里知道,原来现在国家的政策也好,都有免费的药物,而且现在各种药物的治疗都是很有效的。

通过好好服药治疗,没有什么传染性。
深陷泥沼的俞阳在苦苦挣扎时知道了这样的消息,他觉得自己似乎还能看见未来。
俞阳没有让父母知道这件事,他坦言,他们会承受很大的打击,他自己本身承受的打击已经够大。
如果父母知道后万一有个好歹,自己会背负很大的罪恶感,所以他选择隐瞒。
钱有生、俞阳、还有千千万万个艾滋病患者,对他们来说,最难以承受的除了自己与病魔抗争之外,就是对别人袒露自己的病情,哪怕是最亲密的家人。
钱有生没有让儿女知道,俞阳没有让父母知道,他们这么做,是在保护家人,也是在保护自己。

关爱艾滋病患者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艾滋病患者都和钱有生一样,不知道自己怎么感染上的艾滋病。
他们对艾滋病的相关知识,是缺乏的,我们这个社会要做的,就是扩大艾滋病知识的宣传面,更要关爱艾滋病患者的心理健康。
国家、社会都在行动,而每个人其实都应该参与进来,只有深刻了解艾滋病知识,才能够避免越来越多的人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