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主题是“携手抗艾,重在预防”。

重在预防。这种病的病理可怕之处在于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治愈。最近有人讲这个病毒被承认是实验室造出来的,这个不予置评了,人类要毁灭自己,本来就很容易。心理可怕之处在于这个病毒的感染者,与正常人之间有一道怎么也突破不了的隔膜,特别是在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疾病反歧视社会行动,现在大方承认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人已经越来越多,歧视越来越少,而主动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又能有多少?哪怕是和国家领导人握手,马赛克也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的媒体按惯例会公布很多东西,艾滋病情况的严峻、数字的可怕以及社会危害等等,当然还不会忘记强调我们是“低流行区”。
但是鲜有人会关注到和这个病“咫尺天涯”的另一个人群:恐艾者。
这些人,生理上没有感染那种无解的病毒。但在心理上,却始终认定自己已经被感染。因此他们进入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状态。
和一般的心理疾病不一样,因为病因是怕死,所以他们不大会选择自杀。然而这种失去所有希望的生存,比死亡的恐惧不遑多让。
记得以前媒体曾经报道过什么“阴滋病”,说是有一群人拥有了艾滋病的所有症状,自己已经给自己确诊,但是他们的血检,却一直是阴性——这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阴性艾滋病”,是高程度的恐艾症而已。媒体的不求知让这个东西一度成为一种恐慌。

很难描述恐艾者的世界。下面这篇文章,是10年前仵作的一篇作品,真人真事,发表在当年的《南都周刊》上(配图为新加,略为改动了一点文字)。当时年轻气盛,拥有新闻理想的我曾尽力想进入他们的世界,但是没有成功。
恐艾者
他们走进地狱大门,最后回到阳光的世界,经历了整整两个月的黑暗。
2000年,大上海的某个角落,一扇昏暗狭小的门。这扇属于某个不知名的小发廊的门在被一个叫黎家明的醉酒青年推开后,成了著名的“地狱之门”。因为推开了这扇门,黎家明从一个令父母为之骄傲的有为青年,变成了人见人畏的艾滋病毒感染者。
2005年12月1日的深夜,古都南京,一扇很气派很宽敞的门被一个满身酒气的青年推开了。门里的地方有一个洋气的名字——“XXX桑拿会所”。
这名执意给自己化名为“孔扬”(“恐阳”的音译,阳性意味感染——后注)的大学生在一周后惊恐地发现,那天夜里,他推开了一扇“地狱之门”。
风流一次
孔扬说,他想不起来推门的时候,自己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也许是因为酒精,也许是因为他不愿意再想。他记得的是自己踉跄着走进了一个光线很昏暗很暧昧的房间,接着就是一副凹凸有致的躯体向自己凑了过来。
“说实话,我在那次之后,到开始恐惧之间有一周的时间。这一周时间我好几次还想去,把我拦下来的不是良知,而是对钞票的心疼。”孔扬回忆。看得出来恐艾,他并不忌讳狠揭自己道德的伤疤。
网络色情,是虚拟世界的严重社会问题。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孔扬开始认识到艾滋病的威胁,并开始“恐艾”,却正是一家教人如何去“寻欢”的“性息”网站的功劳。
“那次事一个礼拜后,我在这个色情网站看到一个帖子恐艾,主题是怎么样才能不‘中标’。里面提到了要小心艾滋病。看到这三个字,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心‘咯噔’了一下。”孔扬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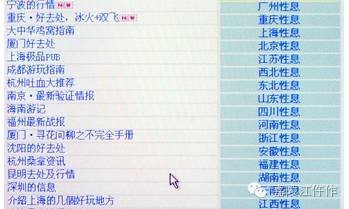
孔扬的网络生活变了,他的搜索引擎的关键词从“性息”变成了“HIV”。短短几天,孔扬关于艾滋病的知识像气球一样地膨胀。最让他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从网上林林总总的知识中总结出感染艾滋病毒后的短期内会出现类似感冒的发烧、皮疹等症状时,孔扬发觉自己发烧了,真的发烧了。
当天夜里,孔扬捂紧了被子,希望自己能流汗,希望自己能痊愈。但他失败了,第二天,额头上那烫烫的感觉还在。
第二天傍晚。当孔扬发现自己因为打了一下午篮球,出了一身透汗却还没有退“烧”时,他几乎绝望。在室友的催促下,孔扬在当天晚上走进了省人民医院。
一场虚惊?
在预诊台,护士看着体温表很是奇怪:你没发烧啊。值夜班的医生心不在焉:你去查个血常规吧。
血常规的结果很快出来了,一向健康的孔扬竟然7项不合格。医生看着单子摇头:血象高,感染了什么吧。孔扬的脸变得跟纸一样白。“医生,你直说。感染了什么?会不会是免疫系统出了毛病?白血病?”把医生问得目瞪口呆。
医生最终只让孔扬打了一针。孔扬从医院回宿舍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搜索着艾滋病人的血常规指标。让他郁闷的是,所有的资料都斩钉截铁:血常规无法判断是否感染艾滋病毒。
也许是因为输了液的缘故,也许本来就根本没发烧,第二天,孔扬感觉自己痊愈了。这个消息让他高兴了小半天。孔扬的推论是:既然艾滋病是绝症,那么艾滋病的症状也不会一治就好吧。
不过就在当天下午,还是那个恼人的网络,把他的兴奋击打得粉碎。艾滋病急性感染期的类似感冒症状是一过性的,很快就会消失!
这一切的描述都和自己的身体症状是如此吻合!艾滋病阴云带来的恐惧让孔扬把大学里学过的逻辑学常识忘得干干净净:如果从A能推论出B。那么未必从B就能推出A。艾滋病感染后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症状,但仅凭借出现一过性的症状这个事实,并不能得出一定感染了艾滋病这个结论。
求助电话
孔扬很快成了行尸走肉。他目光呆滞,行动蹒跚。
孔扬倒没有立即想到自杀。他居然平静地开始设计自己以后的生活,作为感染者的生活。隐居?出家?旅行?无数次选择之后,孔扬觉得,把这段经历公布于世,警醒世人!
“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知道这是自虐,但我就是想惩罚自己。除了父母之外,我想让所有的人来指责我,来歧视我,让我遗臭万年。我就一个念头:我是自作自受,我不得这病天理难容!我那时候特理解受虐狂的心理。”孔扬事后这样回忆。
可是在孔扬拨通报社热线电话的时候,那种对死亡的本能的巨大恐惧,突然像山洪决堤一样迸发出来:对着话筒,孔扬带着嘶哑的哭腔吼道,我要死了!
接电话的记者并没有感到奇怪:灯红酒绿的都市从来就是抑郁症的温床。报社的心理咨询热线经常接到寻死觅活的电话,而热线新闻部的记者们,也不厌其烦地把一个个因为抑郁而自杀的社会新闻写得活灵活现。
而今天的这个电话却有些奇怪:对方吼完这一句后,长久长久,没有另外的声音,电话那头听不见哽咽,打进电话的这个读者在沉默了好久后说,我想见你。

大街见面
见面的地点选择在大街上,这让记者再次感觉到事情不同寻常。“他跟我说他得了艾滋病,我第一反应是,遇到了个精神病人。”
当孔扬把自己的经历和所想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叙述完以后,记者收回了“我遇到了精神病人”这个念头。但是,在孔扬停止述说后,记者张口结舌:对于艾滋病,他几乎也是一无所知,他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好在我看过姚明拍的公益广告,知道一般接触不会传染。否则我想我会拔腿逃跑。”记者这样回忆。
事实上,对艾滋病感染者畏而远之的社会观念,也是“恐艾症”的诱因。很多恐艾者最早是恐惧死亡,接下来他们就发现了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失去一切亲人、朋友,在这个社会上被彻底地歧视、孤立起来。
在著名的“恐艾者”网站上有这么一段“恐友”的留言,题目叫“如果我去检测”。内容如下:“如果医院问我,我肯定说和感染者搞了两年,这样医院就比较重视,查得比较仔细了,这样就不担心漏检了,或者我说和感染者互相输血了。如果没感染的话,对医学界又带来一个思考了,然后医学界就开始反调查我研究我,这样就更惨了,24小时跟踪,看我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然后猛抽我的血做研究,抽着抽着就被真感染了,惨啊。或者他们不信,把感染者的血真输到我体内,惨啊。”
检测之颤
“要过年了,我要去检测。”孔扬在电话里的语气很平静。
艾滋病的检测其实并不复杂。可怕在它有一个“窗口期”,在这个长达6周的期间内,现有的检测手段是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感染了艾滋病毒的。“窗口期”成了众多恐友的噩梦。
屈指算来,孔扬“高危”的日子已经超过了6周。但是孔扬一直无法说服自己去检测。他说,6周后,自己好几次想到过检测,也下过“一了百了,死也要死个明白”的决心,最近的一次已经走进了医院的大门,但是他还是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做好结果为“阳”的准备。恐阳!这才是“孔扬”这个化名的真正意义。
“我看见网站上有个帖子,说一个恐友在检测结果出来的前夜,站在窗前看了一夜月亮。他说,他怕结果出来以后,就再也看不到月亮了。我看完后赶紧跑到了大街上,贪婪地看着周围的人流。我觉得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比我幸运,我觉得他们全部在笑着离我而去。”孔扬的描述里,每个字符都是颤抖的。
高危整8周,离过年还有3天。孔扬抓住了最后的一丝勇气。他来到了南京市第二医院,这个江苏省唯一定点收治HIV病人的医院。陪他一起来的,就是那位唯一听过他倾诉的记者。

这位记者事后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刚到医院的时候,他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进了医院门,他开始颤抖。那是一种能看出来的颤抖。挂号,开化验单,交费,他像一个木头人一样没有说一句话。坐到抽血窗口前,他还是没有说一句话。我觉得他的动作很机械。血抽完了,要自己把血样送到三楼的检验室去。我拉起他要上电梯。他突然说话了。他说,我们走楼梯吧。顿了一顿,他又说,我想慢点上去。”
“血样给了医生后,我和他并肩坐在检验室外的椅子上。他的脑袋低垂着,我实在看不到,也不想看他当时是什么表情。”记者缓慢地回忆着。“我的脑子突然间也是一片空白,我想准备一些安慰他或者是祝贺他的话,可怎么也想不到该说什么。我们靠检验室很近,我能听到里面的测试仪器在响。我的心也在一起响。”
作为一个陪伴者,尚且有如此动魄的心理过程,那么孔扬在想什么?他在经受怎么样的煎熬?恐怕已经难以用言语来名状。
解脱与否
12周到了。孔扬再次找到记者的时候,他已经在前一天去了权威的江苏省疾病控制中心。医生告诉他,8周的结果已经准确了,但既然你还不放心,那就再测一次。省里的测试方法,出结果要在一天后。
在出结果的那一天,下午13:30,江苏省疾控中心上班的时间到了。孔扬再次把记者约到了大街上。接下来的情景,记者用了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
1:45,孔扬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电话”——省疾控中心“艾滋热线”的号码。电话通了,孔扬像触电一样把手机塞给了记者。无奈之下,记者只得替他询问。
“您好,我想问一下艾滋病抗体检测的结果。名字是××。”几秒钟后,传来医生的声音:“阴性,没问题。”“没问题!你安全了!”记者扭过头大声对孔扬说。孔扬抢过手机:“医生您再说一遍!……”挂上电话,孔扬突然跪在了地上,抱头痛哭:“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跟上一次在二院得到‘阴’后的反应,完全不同。”记者回忆说。“我看到他哭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直觉告诉我,能哭,说明他真的解脱了。”
第二天,记者试图再次找孔扬追访,但已无法联系上他,手机换了号码,孔扬从此消失。
文章完,但恐艾者的故事,直到艾滋病被征服的那一天,才会彻底结束
10年后的后记:这篇东西后来被央视制作成了一部专题片。在片子播出后,我的亲人还因为在片中我和恐艾者的一次握手而心存芥蒂。对艾滋病的害怕性歧视,依旧是恐艾者的病根之一。
今天重提旧文,一是为了提醒大家莫忘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二是对奋斗在抗艾一线和恐艾干预一线的医生护士们表示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