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客厅看了《健康之路》节目对佑安医院感染科的徐莲芝主任和吴主任两位大夫的专访,我印象深的只有以下的几句话:“感染者要有信心……”“病人要注意生活的习惯,戒烟戒酒……”“有许多很危险的病人我们都救回来了,有的还恢复了工作……”
看完节目后,我和父亲都被两位医生的敬业精神和真诚打动了,我们作了商量后,当天中午就给徐主任写了一封信,包涵了自我情况的介绍和对治疗方式的咨询。
信寄出去后,我又恢复了在等待希望中的生活。
在第七天的中午我接到了徐主任的电话,她对我说:“小×,你无论如何要来,有机会就要争取,你只要带一点儿住院的压金,其他如真有困难我们再想办法,别灰心,一定要来,我等你……”
我开始了我的求生计划,我稍做收拾就定好了车票准备去北京。这一走真有生死离别之感,老父体弱是不可能陪我去的,他把我送上了去车站的车。我在火车站见到了特地赶来的Z兄,他递给我一个手机和包着1000元的信封说:“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多保重,我们还要见面的。”
我乘车北上了。
面对绝症,医学有时候会显得很苍白,但是无私的友爱与无偿的奉献却会让人燃起信心和勇气

12月的一个中午,我住进了感染科的单人病房。躺下后我就起不来了,一切的入院手续都是护士们代办的。邻近病房的乔兄主动地接过我的行李并来问候我这惟一没有家属陪伴的病人,但强烈的不适使我没有办法与他多聊。
我的病房本应是最冷清的,但每天护士们上班时都来跟我说话。头几天我实在是太难受了,而在验血后的第三天,医生突然问我是否能跟我的家人联络,我感觉到我的情况一定是很差(后来得知当时我的CD4只有十几,徐主任写给我爸的信中说我的病情很严重),我只是不断地请求她们能帮我安乐死。但护士们总是用愉悦的目光和亲切朴实的话来安抚我:“你这算什么,比你严重多的我们都见过,现在都好好地活着……”
医生在12月底告诉我应该用鸡尾酒疗法,中药是不能帮我了,父亲,一个生活简朴的老人寄来了药费,Z兄几乎每天都来电问候。我常常流着泪与父亲交谈,亲情不断地化为力量通过话筒传递给我,Z常让我感到我还有回到社会中再有作为的一天,点点滴滴的友爱在恢复我的信心。
在开始用鸡尾酒药物时我已病得很重:常常高烧不退,半夜发冷,人在被窝里抽搐,连按呼救铃的能力都没了,但我开始乐观了,在我每天有限的感觉稍好的一两小时里,我会与护士或病人家属交流。这里病房真的给我一个家的感觉。
徐主任是一个大忙人,常出差,在京时也要负责艾滋病热线和门诊的工作,但只要她来到感染科一定会来到我的病床边站着和我谈上一个小时。感染科的医护人员在本身没有伤口的情况下来查房都不带手套,在输液后拔针有意外出血的时候护士会毫不犹豫的用手压着棉球帮助止血,我曾想把手缩回,她对我说:“你在贫血,这些血对你很宝贵……”

为了给病人以心理上的安慰,他们付出了太多,而这一切无偿的奉献都转化为病人生存的信心和勇气。
当你生活在这一个充满着爱心的家园中你会被感染的。除了医护人员外,还有一批社会志愿者来帮助病人,他们中有工人、公司职员和医科大学的学生。在我能有信心去面对治疗时,首都医科大的学生们给我送来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每周一换,在农历新年的几天里他们还分批来陪我,给我送来食品。一位姓葛的汽车厂工人更是每月一两次骑一小时的自行车来到感染科看望病人,并给他们剪头发,元旦前、春节前和出院前他给我理发三次,年三十晚上他来到我的病房陪我这惟一的病人过年,另一位在银行任职的郝先生三天两头地来看我,本来我是最孤独的病人,却能尽情地受用着这爱心家园的温暖。
我开始苏醒了,每天的清晨,我会很早地醒来,坐在病床上,在寂静中等候那来自天安门广场升旗的乐声,感受着一种庄严,如果人的良知尚存,那么人性的善良是很容易被生活中一些平凡的事唤醒。
在我的身体得到充分的恢复之前,我已不再倦恋这个温暖的家,我心又展翅了,我需要回到生活中去拼搏,用我的心去告诉那些没有到过“家”的孤儿:我们不是被抛弃的。
我想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也想请大家把我们这些艾滋病患者当成一个普通人。
在听说我要回家的消息时,医护人员都很关心,问我是否担心住院费,我说不是。我托护士长帮我打电话订票,但她为了给我节省几十元的送票费,利用她自己的休息日到车站去给我买。北京红十字会的郝先生主动提出把我送到车站。
离开是在星期天的清晨。一大早5点,护士W就来帮我提行李下楼了,我两个多月没有出来过,清晨的寒风使我难以抵挡,但当我走出大门时,我发现在等我的不仅是郝先生,60多岁的徐主任也在寒风中等着,不自觉地心头一热,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我想用我的经历告诉人们,HIV也是一种机遇,不要把我们当成什么怪物,我们和你们一样也是人,是充满爱心的人。温暖的南方春暖花开,熟悉的街道给我一种亲切的感觉,我的心满怀着重回社会的期望,人生对我又有了吸引力。而我的身体却比去时还要虚弱了。父亲开始看到我的样子很担忧,但我的乐观与开朗安慰了他焦虑的心。
出院前一天做的抽血化验结果表明,经过近三个月的抗病毒治疗后我的CD4水平已上升到52。虽然这还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但和以前相比是好转的迹象,很令人鼓舞。
为了避免细菌感染,我每天尽量留在家中,定时服药、作息,并帮助父亲一起搞家务,闲时阅读各种报纸杂志,搜寻着任何与艾滋病有关的信息。徐主任定期给我写信,询问我的状况,提出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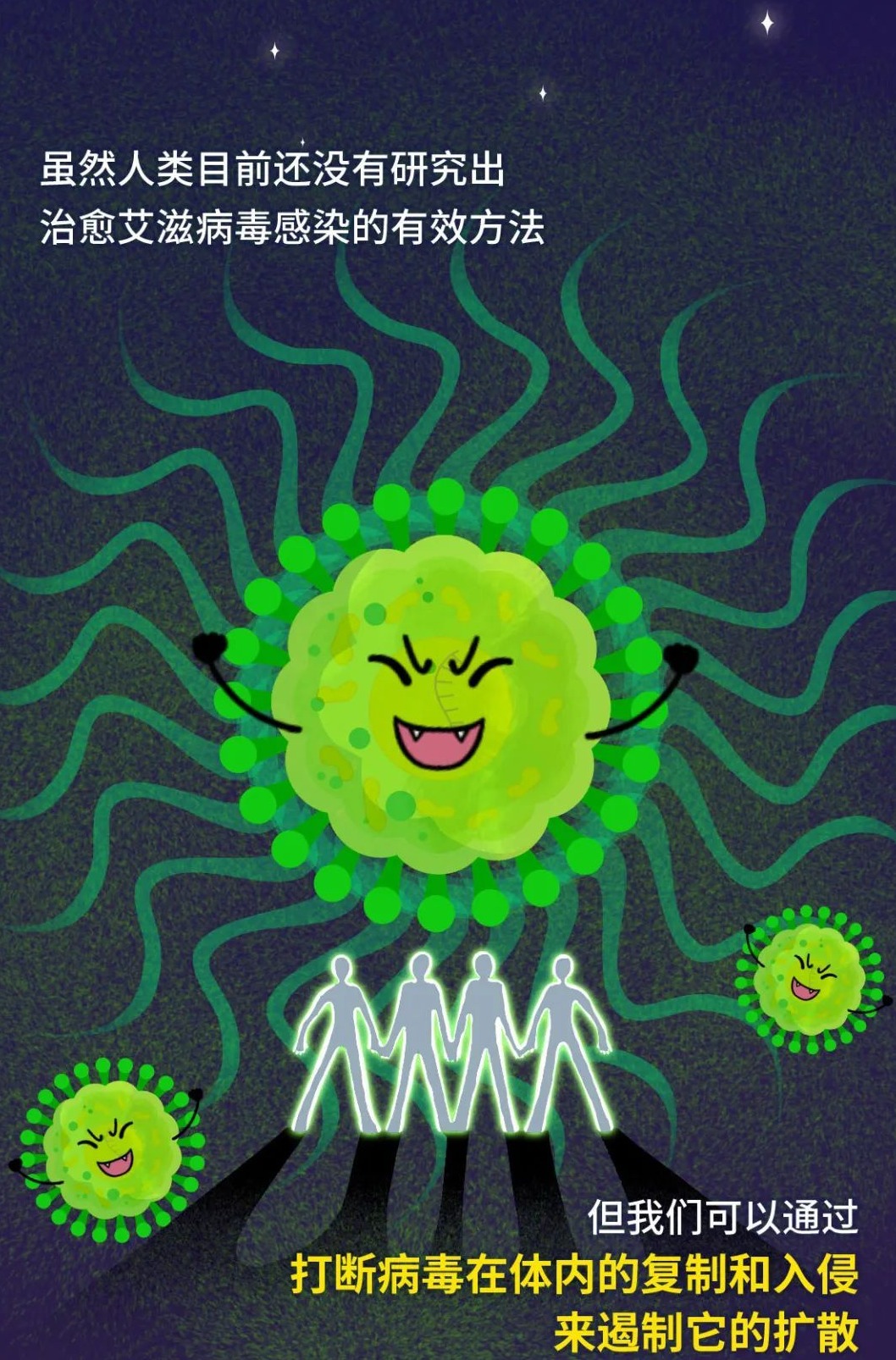
我的胃口开始好转,体重增加,皮肤上的斑点也慢慢地褪去了。一切是那样的令人鼓舞,我准备重入社会。找工作竟然很顺利,经朋友介绍找到了一份收入中等的工作。因为身体差,工作的紧张节奏很快使我疲惫不堪,每天一到家吃过晚饭就倒在床上了。一个多月后,家人发现我有点支持不住了,劝我停止工作。我只好辞职。
我家附近有一间网吧,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在网上我能查寻到更多的新的治疗信息。我发现了一些艾滋网站里充满着恐艾者,完全是由于无知而导致极度的恐惧。同时,我又想到那些同样在痛苦中煎熬的病人,他们是否知道艾滋病是可以治疗的?他们是否知道在发病时在北京有一个温暖的爱心家园呢?
于是,我在网上申请了一个论坛《艾滋病人的交流》,很快就与一些病友建立了联系,彼此之间相互交流着寻医问药的经验,倾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因为去网吧花费太多,我便用那两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配置不高的电脑。
7月中旬,我到当地传染病院做抽血检测,结果CD4上升到104,虽然T细胞的比例依然严重失调,但说明恢复依旧在进行着。传染病院的蔡主任也说CD4能从十几上升到过百是很不容易的。这个结果给我带来更大的信心,我觉得我应让更多在绝望中的病友看到希望,让他们能科学地认识艾滋病不再是死亡的代称。
在论坛上,我将自己的体会和久病成医的一点经验贴上去,比如《用药体会》《可能有用的一点经验》《HIV也是一种机遇》《心声》等很多帖子,希望多一些人能成为我的经历的受益者。

我的努力很快就得到了很好的回报,论坛的点击率不断上升,至今已经有4万次以上,很多感染者与患者向我提出问题,我一一作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相互鼓励、交流、相互帮助。我觉得艾滋病人自述,自己是个对别人有用的人。
除了在网上的交流,我也和网友们通信通电话。因为我是论坛的版主,而且和很多人相比,我似乎表现得更坚强,所以大家都称我为大哥,也许他们有的人比我年龄还大。同时很多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的人更是愿意向我说出心里话,本来他们最怕感染,但他们却不怕接触我,很多人愿意我这个真正的患者陪他们去检测。
我的生活还未稳定下来,沉重的医疗费用负担使我不安。但由于我常常与朋友们交流,互相关心鼓励,我身体恢复得很快,现在体重已达到了发病前的正常水平。上个月检查,我的CD4上升到了168。这太令人兴奋了,我怀着更大的信心去生活。我期望着能重新自食其力的一天。
在佑安医院里,我曾经接触过一些报纸的记者,对他们,我只提药价问题,因为这才是我们这些患者的关键困难,但他们似乎只想问我们是不是恐惧,患了病有什么感受,但却没人关心药价这个实际问题。
因为常上网艾滋病人自述,我知道在南非、巴西等几个国家,政府已经准备不顾一切突破知识产权公约,下令药厂仿制鸡尾酒药物。国际上许多有识之士也在呼吁在艾滋病药物上达成共识,让第三世界的患者吃得起药。
同时我也希望媒体在宣传时不要加重人们的恐艾心理,因为社会上的恐艾气氛越浓,我们的生存环境越艰难。比如中央台《实话实说》节目,其中两位患者的出场方式就都说明了社会上的恐艾气氛。要说这是现实情况下的一种无奈的话,但那个叫“小李”的患者居然说被感染后死亡几率是百分之百,显得如此无知,而且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是一个典型的把自己钉上十字架的恐艾说教者,他在节目上的表现只能使这个社会更恐艾。
所以,我现在想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也想请大家把我们这些患者当成一个普通人,因为我们和大家一样。
我们生活着,我们挣钱养活自己,除了我体内有着艾滋病毒,除了我要每天吃药,我们是一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