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处“社会”之中,不自觉得便开始习得、延续它的规范,回应、遵循它的要求。“社会”这一人造物,为人所造,却反过来造就了人。在这一前提之下,每个人对于自己的了解与意义的获得,将不再来源于个体自身,而是来自于我们身处的社会以及社会中无数的与我们相似又与我们不同的“他人”。于是,对于“疾病”这一本生发于自然领域的问题,探讨其在社会领域内的文化意义,解释个体间、群体间围绕于此所生产的关系及关系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
一、疾病本身:艾滋病的社会意义
艾滋病的发生是因个体感染HIV病毒所引起。HIV病毒通过攻陷个体的免疫系统来达到其繁殖和延续的目的,其结果是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存续形成打击。
区别于医学领域讨论HIV病毒对人体的感染机制及其发挥“侵略”效能的过程,社会学领域对于艾滋病的讨论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以及由这一疾病可能引发的“问题”而展开的。围绕着“艾滋病”这一中心,在研究中分出了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诸多社会因素的研究与讨论。在这里,艾滋病由个体层面被提升到群体及整个社会的层面,对于这一疾病的解释,大多学者选择了从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的角度进行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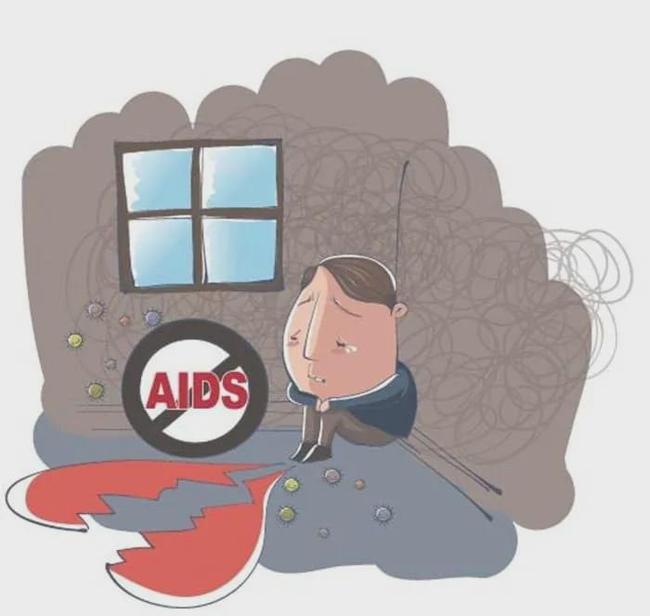
社会学将“疾病”视作一种“失序”,但这样的失序并非个体主观愿意的、推动的,而是诸如经济、阶层等问题共塑的结果,艾滋病作为一种“疾病”,其社会意义在于通过于此可以看到现存的不合理的结构问题,通过研究“艾滋”的生产与传播,可以促进我们改变和修缮现行的制度乃至推动结构的变迁。
二、患病个体:艾滋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的身份建构

正如戈夫曼的戏剧理论,每个人都是在人生舞台上扮演着各种角色。一个人的身份是多样的,取决于他所处的“舞台”。一个携带HIV的感染者,一个艾滋病人艾滋病毒携带者,这样的身份都是因事件发生而产生的个人的新的角色。在获得这一角色之前,他(她)已经拥有了多样的角色身份,诸如家庭角色“儿子(女儿)”或是以职业划分而获得“工程师”、“教师”之类的角色。
不同的角色蕴含着不同的角色期待,而所谓角色期待便是形成于社会对于个人所承担的角色的要求,是一套希望个体能够习得并遵循的意识与行为规范。而这些规范并非是自然性先天产生的,它们的形成实际上应当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要求,不是“天赋的”而是“人为的”。
于是回到有关于艾滋病毒携带者以及艾滋病患者这样的身份本身,我们可以知道,之所以具有这一身份艾滋病毒携带者,是个体被病毒侵犯后社会对个体身份的反应,此身份是后天出现的,而不是先天就具有的。患者或携带者身份的获得与个人的道德无关、也绝不是某一群体所特有。患者或携带者身份只是个体众多身份中的其中一个,并不是可以用于描述个人所有生命体验和价值的唯一身份。


当前部分社会舆论环境中,对于患病者采取单一化其身份的态度,以病人或携带者这一身份为个体生活的不同领域都贴上唯一“标签”,并混淆其各种身份之间的关系,并企图通过将疾病问题与道德相关联,而将病人身份加以消极的刻板印象形成“污名”。就像两台同时开演但是内容迥异的戏,登台的却是另一舞台的主角,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基于此,不将个体价值与单一身份相关联,是当前消除偏见的一条可行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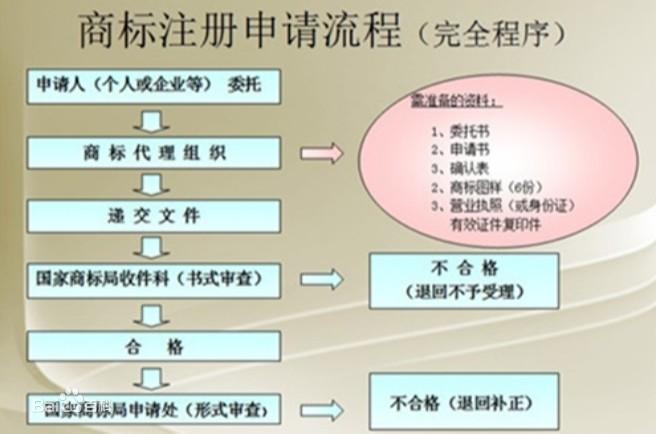
三、患病的个体与“他人”
正如国家间以某座山、某条河划分国界一般,在人类社会之中,人们对于人和事都有着不同的划分标准。这个所谓“标准”,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内涵,直白地说,就是“不一样”。至于不一样的在哪里,就是所处的情境所决定了。
在有关于艾滋的讨论中,最明显的就是“是否感染”、“是否发病”两个界限,前者把携带者、患者与健康的个体区分开,后者则是在同为感染者中依据病程将携带病毒的人们再次进行了区分。在这里讨论的主要集中在健康人与患者之间的区分。

在以往所看到的科普宣传中,大多强调了传播途径、感染后果、行为预防三个方面,对于感染后通过医疗控制可能达到的效果却相对较少提及。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健康人与患病者之间“我们”与“他们”的区分被强化了,在此基础上直接提出消弭差异而实现平等,是有些困难的。
在有关疾病预防的科普中,为兼顾其警示作用并保持相对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对于存有患病风险的人群的描述变得十分重要——是所谓“高危人群”还是“高受害风险群体”,其所传递的语义存在分别,对于后者而言,相当于改变了感染者所处的位置,传递出的文化内涵更为温和而不包含某种特别的歧视。
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通过科普去了解一种疾病的发生及其后果,这无可厚非,也可以通过重新理解科普,转变看待感染者的态度,通过站在他者的角度上反观自身,寻找到自己与他者间保持平等的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