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5日,人类历史上第二例艾滋病被彻底治愈的患者——“伦敦病人”,一度点燃了很多人的希望。
为什么是第二例,又是怎么治愈的呢,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呢?
这就得说到第一例治愈的“柏林病人”,一个同时患了白血病和艾滋病的柏林留学生,在治疗白血病的时候,移植的捐献者的干细胞里,竟然带了能够抵抗艾滋病的基因。
于是神奇的痊愈奇迹出现了。
但是,也只是神奇而已,毕竟历史上奇迹多了去了,并没有实际意义,我们无法确定他的痊愈具体是哪一个因素在主导,这也是医学上孤立不证原则背后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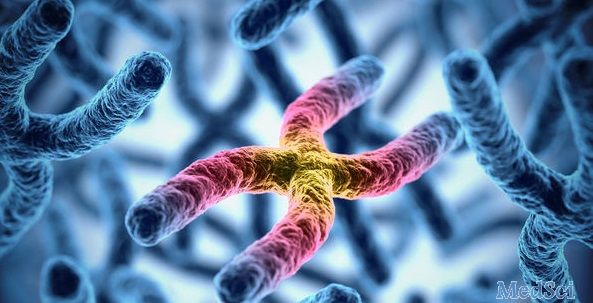
直到第二例的出现,证明了科学家们的归因正确,捐献者的基因里,就存在一个叫做CCR5-△32基因变异,这种变异基因在极少数的北欧人群里都可以找到。
同时,第二例痊愈,也说明了技术上实现变成了可能,这导致这一项技术的前景突然变得明朗了起来。
当然,现在鸡尾酒疗法已经可以让艾滋病患者控制住病情,可以和疾病长期的共存生存下去(不要觉得很恐怖,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和很多疾病共生到死的,只是艾滋病听起来比较恐怖而已),冒险去移植干细胞还是带有风险。
但是,近几年基因编辑技术的大突破,也就是CRISPR-Cas9技术和这件事一结合艾滋病治愈,那么想象力就多了去了,真正可以普及的痊愈已经不远了。

这是一个从个例和奇迹里寻找分子层面的原理,然后在去研究药物和疗法,最后实现医学进步的过程。
这中间靠的是茫茫的个例中寻找奇迹,不断试错,最后找到一两个有效的发展方向,但是未来,等基因编码真相明朗,和编辑技术成熟以后,就会针对性的对某一种疾病进行针对性的手术刀式精确治疗。
从靠运气,靠大量的试错,在到精确的钻研,靶向式的深入研究,这是一种从表现到本质的进步过程。
这个过程,我们往前推,可以发现医学发展史上好几次进步都是如此。

比如在博格创立福泰制药之前,世界制药巨头像默沙东、葛兰素史克研究药物的方法,就是派各种科学家去全世界各地寻找不同的菌种,然后尝试挖掘其中有药用价值的菌种,进行培育和测试。
这是二战之后流行的研究方法, 就是找啊找啊找,靠运气,靠大量的试错。
博格觉得这种效率低,人力成本高,觉得制药就要回归科学方法论,就要针对性的开发艾滋病治愈,通过科学研究提出假设设想,从分子层面进行研究,一对一开发针对性的新药。
虽然博格率领团队研究了好几年,开发出来的药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不过意外的惊喜就是对另一种病有特殊疗效。
其实很多特效药,最终的疗效往往都是偏离初衷的,比如生发剂,比如伟哥,都是意外的产物。
我们在往前推进,看看中国的中草药和现代医学的演化,也是这么一个进步过程。
中国的传统医学,方法论也是从茫茫的植物、矿物、动物中寻找一大堆东西去试验,如果有效那么就做个记录,然后一点点累计和优化。
我们排除老祖先们因为对身体病理了解太浅,从而导致的逻辑错误,药物归因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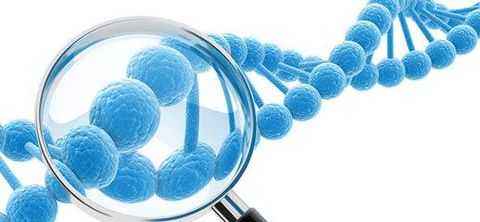
就单单从方法论来说,几千年来,咱们老祖宗们的医学药物获取模式,就是如此,大批量的尝试,碰运气。
直到19世纪,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人们对于人体的了解开始一点点的深入,这种低效率、大规模的试错方法论,开始被针对性的研究方法所取代。
虽然近代对于人体的认知依然有限,依然会出现很多现在听起来毛骨悚然的疗法,比如手术风流行的时代,什么病都切切切,连精神病都要打开脑壳搅拌一下(嘶、、、、)。
但是方法论至少开始进步,开始针对逻辑去推理,用相对科学的方法论去研究了。
从远古时代,人们把病归结为鬼神,一生病就觉得被鬼神附体,然后破脑壳治病(古人觉得脑袋开个洞,邪祟飞走了,病就好了),慢慢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开始回归自身,在到现代医学正确认识自身,从医学哲学(西方四体液,东方阴阳五行)层面,到解剖层面,再到分子层面,一步一步我们走过来,方法一直在进步。
不管是今年3月5日的“伦敦病人”,还是几年前CRISPR-Cas9技术问世,都是下一次医学大突破大惊喜的前兆,我们就拭目以待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