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 | 治愈艾滋病的方法 真的快要出现了?
网易君子
2015-04-20 10:47
0
还记得去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吗?那是根据一个关于绝症患者努力求生、抗争的真实故事改编。而艾滋病的研究者们也在寻找艾滋病治愈方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和抗争。从1981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90年代令人惊喜的鸡尾酒疗法。一种致命的病毒被驯服成了一种慢性症状。下一步就是找到治愈的方法。科学家们天生充满好奇心,艾滋病研究者在这些年中也学会了谦逊。科学的发展总是围绕着种种不确定,其中也交织着挫折和希望。
艾滋病病毒效果图
1981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1981年的一天早晨,我妻子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疗中心值班回家后,告诉我她那里刚接手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新病例。病人名叫Queenie,染着黄色的头发,是个只有十八岁的男妓。刚到急诊室时,他发着高烧,不停咳嗽,似乎是患上普通肺炎。本来他要接受抗生素治疗,但医疗小组在他的肺部里找到了一种名为卡氏肺孢子虫的细菌。这种细菌以能够引发真菌性肺炎而著称,通常发现于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以及接受了器官移植或者化疗的成人体内。
医院召集了几名专家对这一感染症状进行分析。Queenie的血小板含量十分低,这让他很容易出血,我也被叫去对他进行检查。他侧卧着,呼吸困难,床单上浸满了他的汗水。他感染了非常严重的疱疹,以至于外科医生不得不对他大腿被脓疮侵蚀的部位进行了切除。我也无法解释为何他的血小板含量会变低。他的肺开始衰竭,只能依靠呼吸器。不久之后,他因呼吸衰竭死去。
他患上的这种罕见肺炎在东西海岸都出现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免疫专家Michael Gottlieb对其中一些病人的血样进行了分析,并做出了一项重大发现——这些病人几乎丧失了他们所有的辅助T细胞,而这些细胞能够保护人体免遭感染和癌症的侵袭。1981年6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发表了Gottlieb的发现。同年七月,纽约大学的Alvin Friedman-Kien博士在报告中提到,纽约和加州有26名男同性恋者被确诊患有卡波西肉瘤——一种淋巴管及血管癌。该现象也很奇怪,因为通常只有东欧犹太人种或者地中海后裔群族的老年男性才会感染卡波西肉瘤。
我曾负责看护这些卡波西肉瘤患者。当时我只是最初级的职员,不具备肿瘤方面的专业知识

,但没有哪个资深教员愿意接受这种工作。我的首个病例是一个住在西洛杉矶的隐蔽同性恋者,绰号为Bud,是一名中年消防队员。就在他入院后没多久,他的腿上开始长出如成熟樱桃般的增生组织,接着扩散到躯干、脸上,甚至嘴里。尽管按照晚期卡波西肉瘤的治疗标准,他接受了高强度化疗,但肿瘤还是继续生长,不断侵蚀着他的身体和容貌,并在一年内夺走了他的生命。截至1982年,医院中开始出现患有各种恶性淋巴瘤的癌症患者。化疗对他们同样未能起到帮助作用。因免疫系统遭受破坏,病人死于各种疾病。我所有的病人都遭受着一个同样的机体紊乱艾滋病治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同年将这种病症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也就是艾滋病。当时,科学家们尚不知道这种疾病的成因。
次年,两个研究小组——由Luc Montagnier和Francoise Barré-Sinoussi带队的巴黎巴斯德研究所,以及由Robert Gallo领导的马里兰州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描述了在艾滋病人的淋巴结和血细胞中发现的一种新逆转录酶病毒。逆转录酶病毒以一种恶性方式进行繁殖方式:它会永久性地将自己基因中的DNA插入到宿主细胞的细胞核中,为了自身的延续而劫持细胞的机制。当逆转录酶病毒发生突变时(它们通常也会发生突变),人体或疫苗很难盯住并消灭它们,因此它们会不断繁衍。人们曾普遍认为逆转录酶病毒疾病无法治愈。1986年5月,在对这一发现到底应该归功于谁进行了大量争论之后(最终法国团队因
1986年,国际科学委员会最终将此病毒命名为H.I.V.,并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病症
此荣获了2008年的诺贝尔奖)艾滋病治愈,国际科学委员会最终将此病毒命名为H.I.V.,即人体免疫缺损病毒。截至当年年底,在近两万九千名确诊患有艾滋病的美国人中,约两万五千人死亡。
自那时起,艾滋病变成了一种可以治疗的病症,这也是现代医学在对疾病抗争中的伟大胜利之一。1987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了一个艾滋病患者使用的药物AZT,它曾是一款流产的癌症药品。起初,这种药物十分昂贵,而且处方剂量很大,后来还被证实具有一定毒性,因此引起了同性恋团体的反对。但AZT能够在病毒形成时潜入其DNA中,后来人们减少了它的使用剂量。目前,科学家们已经开发出三十多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可阻止艾滋病毒在辅助T细胞中繁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一种联合用药疗法——“鸡尾酒”疗法
它借鉴了肿瘤学家对治疗癌症采用的治疗方式。同艾滋病毒粒子一样,癌细胞能够迅速变异,逃脱单一靶向药物的追踪。一些著名的研究人员,比如来自位于纽约的Aaron Diamond艾滋病研究中心的David Ho将治疗方案——HAART,也被称为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投入到临床试验中。我将这种“鸡尾酒”给我的一位病人David Sanford服用,疗程开始不到一个月他就退烧了,感染症状消失了,精神和体重也开始恢复。他血液中的艾滋病毒几近清除,而且没有复发的迹象。随后,Sanford在一篇普利策奖获奖文章中写到,“或许我被卡车撞死的几率甚至高于死于艾滋病的几率。”现在美国大多数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状态应验了这句话。在过去的五年中,我所照顾的众多艾滋病患者中没有一人死于这种疾病。
但路途依然坎坷。目前,全球共有艾滋病携带者3500万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带,这一艾滋病新增病例最多的地区,百分之六十三有资格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并没有获得治疗;即使那
些接受到治疗的患者也没有得到完整的医治。在美国,平均每个病人接受一年 HAART 治疗的费用要达到数千美元,长期的副作用也会让人的身体变得衰弱。
现在,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开始探讨艾滋病的治愈方法了。我们对艾滋病毒的了解程度已经达到了我们对某些癌症的了解:人们对艾滋病毒的基因进行排序,并破译了它侵入宿主细胞的方式,并以三维图谱的方式描绘出它的蛋白质。1997年,一项重大的发现腾空出世:该种病毒能够潜伏在长寿命的细胞中,而目前的药物无法对其产生影响。如果我们能够以安全且经济的方式清除病毒贮主的话,我们将最终战胜艾滋。
1983年1月1日,旧金山综合医院开设了美国首家艾滋病门诊Ward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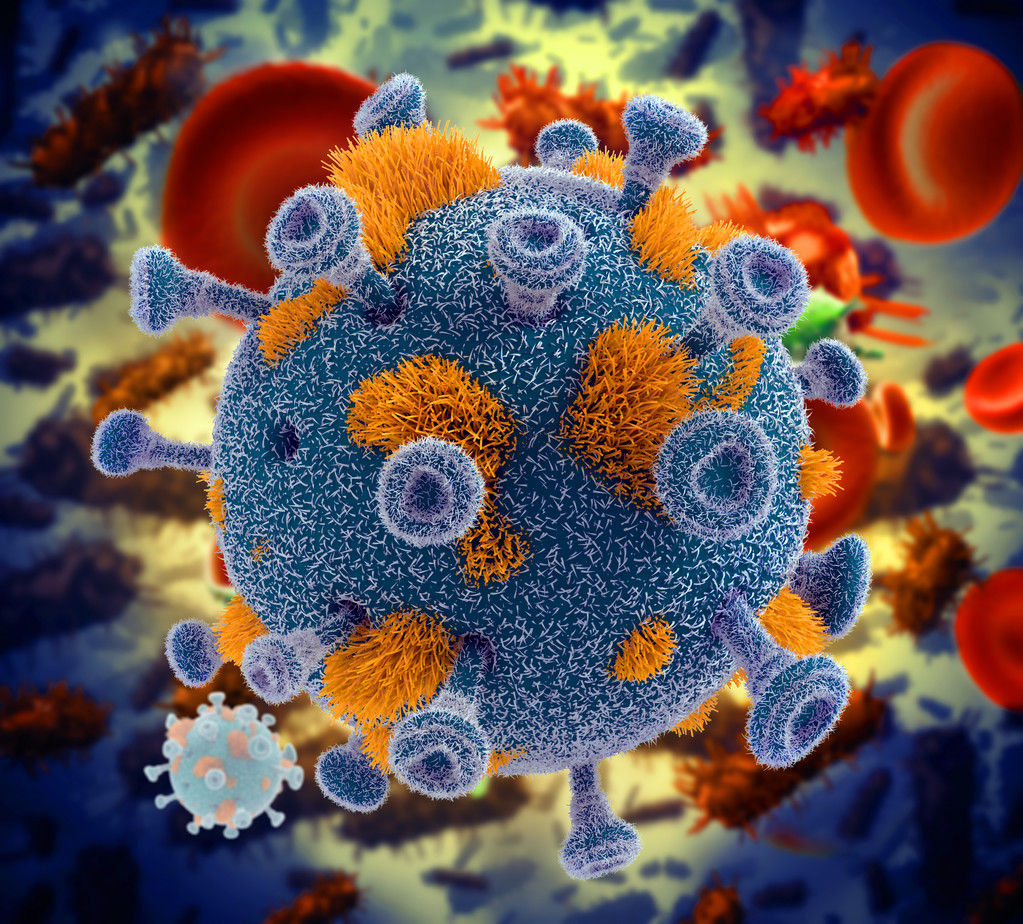
最近,我去那里看望了Steven Deeks,他是艾滋病引发的慢性免疫活化和炎症方面的专家,也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的教授,同时他还从事着SCOPE 研究:以两千名艾滋病呈阳性的男女患者为研究对象,针对病毒对人体产生的长期影响进行测量。每年,这些血液样本会送至世界各地的实验室。Deeks的任务就是将艾滋病毒对人体组织的损害进行分类,并测试那些可能有效的新药。
该门诊占据了校园北边一栋艺术装饰风格大楼整个第六层的空间。我在Deeks的办公室找到了他,他穿着法兰绒上衣和新百伦的跑鞋。他向我解释了他对鸡尾酒疗法的顾虑。“抗逆转录药物的目的在于阻止艾滋病毒进行复制,它们确实很有功效,”他说道。但很多病人无法借助药物完全恢复健康。免疫系统得到改善,足以阻止艾滋病,但因为这种病毒很顽固,免疫系统必须做出持续的低水平响应。这会带来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组织产生损伤。
美国旧金山综合医院,首家艾滋病门诊ward 86在这所大楼的六层
炎症也会因药物产生的副作用会加剧。早期的治疗会引发贫血、神经损害和脂肪代谢障碍——脂肪从四肢和面部消失,并在腹部沉积。脂肪营养不良仍然治疗艾滋病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Deeks发现SCOPE 研究对象中的很多病人胆固醇和甘油三酸脂较高,这些将会导致组织损伤,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则是似乎由动脉壁炎症引发的心脏病。Deeks也发现他病人中出现了肺癌、肝癌和皮肤癌患者。在这种传染病早期的反复症状中,他发现中年患者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患上其他疾病:肾脏和骨头疾病,可能还会产生神经认知缺陷。据Deeks看来,艾滋病更好的定义或许应该是“获得性炎症疾病综合症”。
他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位病人,我把他叫做“Gordon”。一位高个子、戴着无框眼镜的和善男子起身和我握了手,我看到他标志性地凸起的腹部。他身患艾滋病已经将近四十年了,他说他感到很幸运能活下来:“我一位长达十年的伴侣也患有相同的艾滋病,我们吃一样的食物,找过同样的医生,早期接受相同的艾滋病治疗,他在1990年6月就去世了,那大概是在25年前。”
他告诉我:“我不再担心艾滋病毒本身了。我更担心我的内脏和提早衰老。”1999年,他在五十岁时得知,脂肪沉淀会令一条主要动脉的血流大幅度缩减,而这根动脉是心脏左心室的主要养分供给动脉。他行走时开始感觉到疼痛,原因是骨组织的血液供给减少了——这种
因为这种病毒很顽固,免疫系统必须做出持续的低水平响应。这会带来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组织产生损伤。 据Deeks看来,艾滋病更好的定义或许应该是“获得性炎症疾病综合症。
情况称为“缺血性坏死”。2002年,他进行了第一次髋关节置换术,2010年又做了第二次手术。他的肌肉已经萎缩,坐着的时候都会感觉不舒服,所以他有时得穿着特制的泡沫软垫内裤。每隔一年,他就要往脸部注射聚左旋乳酸用以替代失去的结缔组织。
Gordon生命的延长以及他为了维持生命所用的大量药物,可以说是无数艾滋病患者经历的典型。他所接受的最先进的治疗每年需花费十万美元。尽管这些费用由他的保险和加州政府来支付,但是他将其称为“赎金:是要钱还是要命。”对Deeks来说,问题是“全世界能够找到足够的资源来建立一个每天为大约3500万患者(很多患者身处贫苦地区)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系统吗?”他对此持怀疑态度,这也是他集中精力去寻找艾滋病治愈方法的原因。“我们的理念是,为了治愈艾滋病,我们需要知道它在哪里出现,以及它为什么如此顽固,”他说道。
事实证明艾滋病毒更为聪明。它休眠在宿主DNA链中,鸡尾酒疗法无法对其产生作用,随后病毒将复苏并破坏人体免疫系统
1997年,人们对HAART疗法深感欢欣之余,第一次对彻底治愈的方法予以认真思考。迟早所有感染的细胞都会自己消亡。将正确药物准确结合在一起会一劳永逸地消灭病毒吗?同年,David Ho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从数字上预测了接受 HAART 疗法的艾滋病患者可在28到37个月内战胜可以检测到的病毒。这一期的《自然》也刊登了一篇来自Robert Siliciano(现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员)的不同报道。Siliciano在一种辅助T细胞中发现了艾滋病毒,这种辅助T细胞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提供记忆,通常它们的寿命长达几十年。记忆T细胞极其重要:它们能够识别出感染中的抗原,并做出迅速反应。但是事实证明艾滋病毒更为聪明。它休眠在宿主DNA链中,鸡尾酒疗法无法对其产生作用,随后病毒将复苏并破坏人体免疫系统。
Steven Deeks教授(左)和Robert Siliciano教授(右)
Siliciano夫妻关于艾滋病毒的基础发现
Siliciano现年62岁,在艾滋病研究领域备受推崇。他和他的妻子兼合作者Janet相识于20世纪70年代,Janet今年57岁,有着一头红色卷发,她在Bob的论文发表于《自然》杂志之后加入了他的实验室。她说这个观点出自Bob,但Bob告诉我Janet在接下来的七年中发展了这个观点,追踪那些持续以HAART疗法治疗的病人体内休眠病毒的水平。她的数据证明了他的论点:这种病毒几乎能够无限存活。“我们计算出,若要将所有记忆T细胞杀死,需要持续进行长达七十年的HAART疗法。”她说道。
Siliciano向我讲述了他第一次在一位接受HAART疗法的艾滋病患者身上的记忆T细胞上发现潜伏病毒的情景。当时以为这位病人已经治愈。“我们在任何能想到的地方都对他进行了活组织检查,谁都没发现任何艾滋病毒,” Siliciano说。研究人员取了二十管该病人的血液,将T细胞分离出来,然后把它们放在多个试管中,然后将这些样本与未感染艾滋病的人体细胞混杂一起。如果健康的T细胞受到感染,那么艾滋病毒就会开始繁殖,并被释放出来。如果出现蓝色,说明存在病毒。Siliciano记得他正坐在桌前和一位到访者在交谈,突然一位研究生闯了进来:“那些试管变成蓝色了!”,他回忆道“那一瞬间十分奇特,因为它证实了这种假设,这是激动人心的,但也是一个灾难。大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尽管采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这些细胞还是顽强地生存着。”
很多新的艾滋研究都建立在Siliciano夫妻关于艾滋病毒隐藏在宿主细胞的基础发现之上。通过使用一些有效的化学物,他们能将艾滋病毒从它们在记忆T细胞的隐藏之处提取出来,以此评估病毒在体内的扩散程度,并开始对它们可能分布到的其它身体部位进行标记绘制。
这两个案例证实了研究人员在攻击潜伏性感染上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验证:人体内潜伏的艾滋病毒或许是可以去除的。去除方法可能充满风险且具有毒性,但这仅仅是概念性的验证。
尽管研究人员沮丧意识到这种药物疗法本身不是能够治愈艾滋的良方,但他们最近发现的三个不同寻常案例令人鼓舞,让他们继续坚持寻找治愈艾滋的方法。
第一个案例为Timothy Ray Brown
作为首例且唯一一名艾滋病痊愈者,Brown被称为“柏林市病人”。2006年,在他发现自己患有艾滋病之后十多年之后,他被确诊患有一个同艾滋病毫不相干的疾病——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这是一种骨髓癌。在接受初期治疗之后,白血病再次复发。Brown需要进行骨髓移植。他的血液专科医生Gero Huetter提出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建议,他们使用了一名无法产生CCR5蛋白质(CCR5蛋白质为艾滋病毒进入辅助T细胞的途径)基因突变的捐赠者的骨髓。2007年2月7日,Brown接受了骨髓移植。一年后,他做了第二次移植手术,到2009年,通过对Brown的活组织检查发现,病毒毫无踪迹,他的T细胞数目也回到了正常水平。
Brown最终得到治愈可谓惊世奇迹,但是难以复制,他的医生用放疗和化疗两次摧毁了他自身的血细胞,并通过移植干细胞两次重建了他的免疫系统。这种
做法危险性极高,花费也极为昂贵。研究人员想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创造一种缩减版的治疗方案。第二个案例:两位接受HAART治疗的艾滋病患者因为患上淋巴癌而接受骨髓移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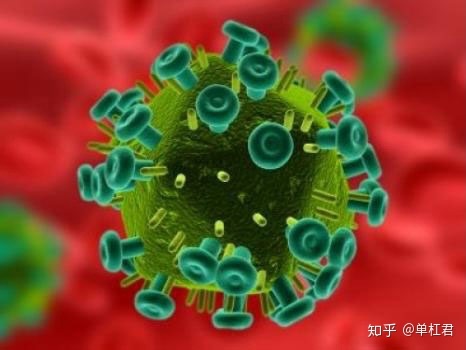
2013年,波士顿布里格姆妇女医院的医生们汇报了一项研究的成果,这两位与Brown不同,其骨髓捐献者并没有产生CCR5变异,接受的化疗强度和密度不及后者。接受移植之后,他们暂停了几年HAART治疗,虽然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没有检测到艾滋病毒,但最终病毒还是重新出现在他们体内。
第三个案例:“密西西比婴儿”
2013年7月,第三个案例的结果也出来了。2010年,一位患有艾滋病却没有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母亲生下了一名人称“密西西比婴儿”的女婴,婴儿血液中带有艾滋病毒。出生之后三十小时,这名新生儿开始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数周内,其体内的病毒数目降低至可检测水平以下。婴儿十八个月时,未能遵守医嘱,中断了治疗。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女婴的血液中没有发现病毒的踪迹,研究人员推测,那次早期的HAART治疗或许阻止了病毒形成休眠存储池。然而,在女婴停药27个月后,她的体内被检测出携带病毒。尽管研究人员觉得早期干预能够暂时驱逐艾滋病毒,但她还是没能得到治愈。
8月,Janet和Robert Siliciano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布里格姆男患者和密西西比婴儿的文章,提到这两个案例证实了研究人员在攻击潜伏性感染上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柏林病人则是一个更引人瞩目的案例。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Karl Salzwedel告诉我,在Timothy Brown案例出现之前,“我们尚不清楚如何才能够去除最后一丁点残存病毒”。Brown的案例提
供了一个“概念性的验证:人体内潜伏的艾滋病毒或许是可以去除的。去除方法可能充满风险且具有毒性,但这仅仅是概念性的验证。”
美国致力于寻找艾滋病治愈方法的最新主力是Martin Delaney合作实验室,该实验室由(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N.I.H.)资助,于2011年启动,它联合了多个临床实验室、研究实验室和制药公司。在所有各方支持和开放交流的前提下,联邦政府对实验室头五年的资助额设定在7000万美元。Salzwedel 告诉我N.I.H.为三项应用进行资助。“每一项都在采取不同的互补方式,试图开发出一种能够根除艾滋病的战略,”他说道:增强病人的免疫系统,操纵CCR5基因,并破坏病毒存蓄池本身。它们代表着对Siliciano理论和从Timothy Brown案例获得经验所作出的不同反应。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实验医学部负责人Mike McCune从借助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根除艾滋病毒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从该病毒发展的早期观察中获得启示:患有艾滋的母亲生出的婴儿在子宫中感染该病的几率当时只占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尽管他们在整个妊娠期都会接触到病毒。
最近,McCune和他的同事观察到发育中的胎儿免疫系统不会对母体细胞产生反应,母体细胞能够轻易地穿过胎盘,最后到达胎儿组织。相反,胎儿体内可产生特种T细胞,可抑制对母体产生炎症反应,这或许也能预防对艾滋病毒的炎症反应,继而阻止病毒在子宫内的迅速传播,从而对婴儿产生保护。
患有艾滋的母亲生出的婴儿在子宫中感染该病的几率当时只占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尽管他们在整个妊娠期都会接触到病毒。
2013年7月,一位患有艾滋病却没有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母亲生下了一名人称“密西西比婴儿”的女婴
McCune与Steven Deeks和 SCOPE 研究合作了多年。当我在旧金山采访他时,他说道,“免疫系统中存在着阴和阳。我们试图将子宫中发现的那种精妙平衡的核心重现出来。” McCune目前正从事干预研究,以此预防成年人因艾滋病引发的炎症,他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在子宫中发现的平衡。他也在研究一些能够让免疫系统在艾滋病毒暴露出来时,更好识别并摧毁病毒的方法。这些研究目前正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身上进行,可能在一到两年内发展到人体试验。

在西雅图,一个由Hans-Peter Kiem 和Keith Jerome负责的小组正在采取一种更带有未来主义色彩的方式从事着研究。他们使用一种叫做“锌指核酸酶”的酶,令CCR5基因失效(CCR5为感染T细胞的必经之路),从遗传学角度改变血液和骨髓干细胞。研究人员将会在体外对干细胞进行修改,这样当把这些细胞送回体内时,血液中的部分T细胞将会对艾滋病毒产生抵抗力。他们希望,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细胞将开始繁殖,而病人则会慢慢建立起一个能够抵御艾滋病侵袭的免疫系统。这些病人体内仍可能残留一个小型的艾滋病毒存储池,但是他们的身体将具备控制感染的能力。
David Margolis领导着最大的合作实验室,该实验室位于北卡罗来纳大学,拥有超过20名成员。Margolis是一位传染病专家,他直接以艾滋病毒的存储池为目标。他的想法,也称为“激活-消灭”,旨在将休眠的病毒激活,揭开携带病毒细胞的面具,然后对它们进行破坏。2012年,他发表了将药物伏立诺他 ( vorinostat )运用于休克疗法的临床试验结果,该药物最初针对T细胞血癌研发。今年十月,当合作实验室的团队与数百名其他研究人员、各种学者和有兴趣的非专业人士齐聚N.I.H.时,“激活-消灭”疗法受到了广泛的探讨。讨论中,Margolis和他的团队探索了各种可将病毒从休眠状态激活的新方法。
消灭阶段更具有挑战性,因为这些被激活的细胞携带着少量的艾滋病抗原,致病粒子释放出的有毒标记在受到攻击之前会被免疫系统识别出来。达成消灭战略途径之一源自一种并不常见的艾滋病患者,这些患者可能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与病毒“和平共处”。其中一些所谓的“精英控制器”或杀手T细胞带有细胞毒性,可以对产生病毒的细胞进行攻击。目标是通过“治疗性疫苗”让每位艾滋病人体内都带有精英控制器,让病人自发产生杀手T细胞。
研究人员也试图关闭一种名为“PD-1”的分子,人体依赖这种分子抑制免疫系统。在黑素瘤和肺癌病的临床研究中对PD-1采用了钝化处理且产生了功效,而且一位病人似乎通过单纯注射百时美施贵宝制药公司提供的PD-1封阻剂治愈了丙型肝炎。
在合作实验室之外还有一些团体,他们也在测试各种艾滋病的治愈方法,并分享他们的结果
除了西雅图团队,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博拉姆逊癌症中心的转化研究主任Carl June和他同事们利用遗传工程来关闭CCR5通道。他们在今年三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最近的临床试验报告,指出改良T细胞能够在艾滋病患者身上存活数年。总部在加州,致力于治愈艾滋病的Calimmune公司也在做着类似工作以去除CCR5(该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为David Baltimore,他因发现逆转录酶——一种在逆转录复制中的重要酶而荣获诺贝尔奖)。丹麦和西班牙的团队也取得了进展,2012年,法国研究人员分析了Visconti研究,该研究将密西西比婴儿早期接受的干预治疗转为正式试验。一个由十四名艾滋病患者组成实验对象小组,他们感染在后的数周内接受治疗,然后中断HAART 治疗。数年之后,他们体内都没检测出病毒。
在艾滋病毒肆虐的最初几年,从来没有想过未来的病人将会活到八十岁。一种致命的病毒被驯服成了一种慢性症状。下一步就是找到治愈的方法。科学家们天生充满好奇心,艾滋病研究者在这些年中也学会了谦逊。科学的发展总是围绕着种种不确定,其中也交织着挫折和希望。
与艾滋病抗争的道路同我们对很多种癌症抗争的过程类似。20世纪50年代,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儿童白血病几乎就是致命的。最后,人们开发出可以缓解这种癌症数月或几年的药物,但是它总会复发。20世纪70年代,研究人员发现白血病细胞潜伏在中枢神经系统中,随后才研发出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来清除它们。时至今日,儿童白血病的治愈率已达到九成。
今年7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二十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来自莫纳什大学的传染病专家Sharon Lewin说,“目前,我们或许还在寻求尽力取得长期的缓解。”大部分专家都认为缓解是可实行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将能够让病人摆脱掉终身治疗。
甚至最为谨慎的艾滋病研究者都认为,在长期的缓解治疗之后,最终将实现艾滋病的治愈。Robert Siliciano告诉我,“首要目标就是要缩减艾滋病毒的存蓄池。这不仅仅是为个人考虑,而且会对公共健康产生影响。”不管患者停止接受HAART治疗多久,医生们都能够将资源转移到那些仍然需要治疗的病人身上。
David Margolis相信他的“激活-消灭”战略将终将奏效,但可能需要十到二十年时间。Siliciano夫妇也同意仍需进行更多的研究。他们说到“激活-消灭”需要用到的药物将不止伏立诺他 ( vorinostat ) 一种。最佳疗法要等到清晰准确地检测出体内含有多少潜伏病毒时才能确定下来。只有多年追踪那些脱离了所有药物的患者才能明确是否找到真正治愈艾滋的方法。“我们了解越多,需要回答的问题越多。”Janet告诉我。
然而,那些早已得出答案的问题依然让艾滋病科学家们感到惊讶无比。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艾滋病毒肆虐的最初几年,我从来没有想过未来的病人将会活到八十岁。一种致命的病毒被驯服成了一种慢性症状。下一步就是找到治愈的方法。科学家们天生充满好奇心,艾滋病研究者在这些年中也学会了谦逊。科学的发展总是围绕着种种不确定,其中也交织着挫折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