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韵贞:艾滋病治疗中国第一人
很多人说过:“曹大夫厉害。”不仅在于她业务好,更因她为中国艾滋病的治疗开了局——她是第一个把检测艾滋病毒含量的仪器和试剂背回国内来的人,还引进了价值100多万美元的免费抗艾滋病药物;她也是第一个把何大一领到中国内地来的人,“鸡尾酒疗法”从此在全国铺开;她带过的一线医生,如今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遍布全国,他们都叫她“艾滋病治疗中国第一人”。
撰稿/李宗陶
曹韵贞1941年5月生于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1963届毕业生。毕业后在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攻肝炎与肝癌的临床研究,1986年转向艾滋病领域。1990年起在何大一教授主持的艾伦·戴蒙德AIDS研究中心任研究员,成为世界上第一批系统研究艾滋病毒发病机理的医学家。1993年起参与“鸡尾酒疗法”的病毒学研究工作,并致力于中外医学专家的学术交流。
1998年出任卫生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副主任、临床病毒实验室主任,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特邀委员。2002年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副主任,临床部主任;受聘于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及临床组组长。2007年7月退休。著有论文150多篇,摘要100多篇,书8本。
很多次,曹韵贞微驼着背,以她特有的步子慢腾腾走到投影仪旁边开始讲课,或者穿过某家医院的艾滋病门诊、病房,留一个厚实的背影。在上海弄堂口或北京胡同里,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背影,有点老态,稳稳当当。
但她又是异常敏捷的。她的眼睛不会转弯,总以高强度的一束小光直射人或物,当场洞穿。所以,当她在第一时间说出“好”、“对”或者“不对”、“不行”时,没什么好奇怪的。这不,我刚把录音笔掏出来放在茶几上,她已从较远的藤椅上一个小跃起,坐到离录音笔最近的沙发上。既是答应接受采访,她便爽直地配合。
很多人说过:“曹大夫厉害。”不仅在于她业务好,更因她为中国艾滋病的治疗开了局——她是中国第一个把检测艾滋病毒含量的仪器和试剂背回来的人,还引进了价值100多万美元的免费抗艾滋病药物;她也是第一个把何大一(David Ho)领到中国内地来的人,“鸡尾酒疗法”从此在全国铺开;她带过的一线医生,如今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遍布全国,他们都叫她“艾滋病治疗中国第一人”。
在各种学术场合,她有一说一,不来虚的,这是另一种厉害。在这个云集了政府官员、科学家、临床医生、法学家、社会学家、富豪以及民间英雄的圈子里,她风格明显,富有权威感,却不给人以权力压人的感觉。曾在某些充满外交礼仪的场合遇见她,看她飞快应付着,看她趁人不备转过头来,冲“自己人”眨眨眼睛。
退休。她保留了有限的几样职务,譬如几家医学杂志的主编、编委,其余一律不兼职、不挂名,“我不要藕断丝连”,她说。
茶几上一本讲清朝皇帝的书看了一半,她还打算把明朝皇帝一个一个看过来。“昨天在翻一本烧菜的书,第103页上,讲八宝鸭怎么烧。多少年了,天天6点钟起来……现在,我要去照顾小外孙、要为自己活了�牎�66岁的曹韵贞宣布道。
跟赤脚医生进村,也蛮开心
我爸爸早年开皮鞋店,被划为资本家。虽然我3岁他就去世了,但从此就背了个“出身不好”的包袱。妈妈28岁守寡全心全意抚养我们姐妹,要求很严,要我们成为国家栋梁。我从小学开始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想好好改造自己。17岁高中毕业时受到第一次打击:学校保送我去复旦大学新闻系,但市教育局因“出身不好”拒批,我就报名去北大荒锻炼,但班主任排除一切政治干扰劝我考大学,后来就以高分进了上医。
1963年我得了全国医学院毕业生比赛第二名。虽然出身不好,但因国家需要人才,就留在中山医院了。我知道这是上医党委第一书记和校长的决定,我参加全国比赛时,他们在场,记住我了。后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下台了,被批斗,去世了。
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奏开始。家被抄了,我妈辛苦一生的积蓄被抄得一干二净,整栋房子被强占,我们被赶到像饭店厕所那么大的两个房间里,厨房和厕浴六家人共用。我成了“黑九类子女”,在医院也是三等公民,不能参加一些会议,不能写大字报,被分配做大量的门急诊和病房抢救工作。因祸得福,反而比同辈人得到更多的业务锻炼。当时好多有真才实学的老医师被下放到门、急诊,我尽可能帮助他们应付造反派,比如要他们倒病人的痰杯、大小便,拖地板,我总是提早上班,不让造反派看见就帮他们做掉了。他们也手把手教了我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临床经验,真是得益匪浅。但是,从1965年到1978年,我们没有看过一本医学杂志,图书馆的外文杂志不是烧毁就是封存。
这当中我四次下乡,总共呆了6年半。没什么好怨的,谁让你出身不好。我只记着妈妈的训导: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1971年我被派去安徽一个偏僻山区,我身上只有两支青霉素、一瓶红霉素,要带6个护技人员巡回医疗,还要负责县医院的会诊。药不够用,我就开始自学中医中草药,带着队员上山采药,跟赤脚医生进村巡回时对症下药,民间真的有妙方。
有一天,县医院来了一个农民,瘦得像柴禾,伴有高热和脓痰,X光显示两肺37只脓疡,县医院说治不了,要他去省城,他没钱就要回家等死。我想来想去,决定试试用鱼腥草,你知道,如果治不好,一顶阶级报复的帽子就要扣过来。腊月天里,我拿着鱼腥草的图案请教农民,终于找到一片沼泽地,那里新鲜的鱼腥草根取之不尽。每天用新鲜的根熬汤,给那位农民服用一个礼拜下来,高烧退了,一个月后,脓疡明显减少,病人开始坐起,三个月之后病人重了30斤,完全好了;我还用半边莲治好了嗜神经毒的蛇咬伤,等等。当时报上也登了,不过都归功于赤脚医生,并没有我的名字。
“放洋”和第一次回国
大学学的是俄文,虽然我妈一直省吃俭用想送我“放洋”,但当时受的教育让你觉得留洋就是崇洋。直到1973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中外关系才慢慢恢复,医院开始有外宾来参观,也开始选拔医生脱产去学英语,我很羡慕,但知道自己没资格,也不敢想。
我妈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就想,为什么不自己学英语呢?1976年,上海第二医学院谢大任教授编了四册《医学英语读本》,可我连ABC也没学过,买了也不懂,就跑到旧书店,二角一分钱买了本《英语语法通读》开始自学,那时候我已经35岁。两年下来,我可以翻着词典看医学杂志,但不会讲、听和写。
1979年我算是第一次政治上大翻身。那一年,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赵行志率120人的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团里有12岁的杂技演员,也有78岁的政协委员,大部分是60岁上下刚复出的领导干部,从心脏病到糖尿病什么都有。市委要求派一个女医生艾滋病治愈,60年代毕业的,要求业务全面、动作迅速的。我们医院当时的院长裘麟教授刚好从“劳动改造”中解放复职,马上点名让我去。“领导委任出国”在当时是政治上翻天覆地的大事啊,就是说你是被信任的人了。我接到通知,半天目瞪口呆。离启程还有一个半月,我从路边电线杆的招贴上找到一个教日文的老师,自己掏钱去学日文。
一进羽田机场,那感觉比起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才恍然大悟自己是“坐井”38年,才明白为什么我妈为我不能留洋学而耿耿于怀的原因。踏上自动电梯,使馆陪同人员在耳朵边上一个劲地说“小心脚下,小心脚下”——5岁那年妈妈曾带我在当时大新公司乘过的呀,可那自动电梯从此沉睡好多年�犇且豢陶媸牵�我脑子里像开飞机一样,多少念头涌上来,恨时光不能倒流,后悔自己虚度年华。这一夜失眠,从此,我决心争取“放洋”。
我当时的主攻方向是探索肝炎与肝癌的关系,正在做170例肝炎病毒五项指标测定。1981年,哈佛大学一位流行病学的年轻教授来访问,科主任临时叫我去接待,我用中文加零星的英语单词跟他说起这170例,他很感兴趣,临走留下名片要我等文章刊出后寄给他,我照做了。在他的推荐下,1981年6月26日,我去了费城Fox Chase Cancer Center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Dr. Blumberg�煾窝卓乖�的发现者�� 的实验室,他的助手Dr. London 教授成了我的老板。Dr. London是个皮肤科专家,是美国第一个报道卡波氏肉瘤与艾滋病感染有关的医学科学家。费城一呆两年半,我接受了正规而严格的实验室训练。英语从一句不会讲,听见电话铃响只会发愣,进步到听说读写虽然不是很好但完全可以应付。
1983年,医院写信来要我回国。Dr.London一再挽留,我谢绝了,带了一些仪器、试剂回国。回来以后破格提了副教授,一年后出任免疫室主任。我们这批人,真的是想为国家做点事的。
但那时候做科研很困难,什么都没有。我当时算是杰出青年科学家,什么三八红旗手、卫生部劳模、上海巾帼奖第一名,荣誉一大堆,还拿过5万元青年科学家的基金,但对科研来说,这是杯水车薪。我拿出了在美国两年半的工资,购买实验设备和试剂,建立了中国的肝癌细胞株,但还是缺钱,做不下去。当时国家政策不像现在,对归国人才有一整套政策支持,而且气氛也不正常,如果做成了,人家就说,他国外回来的,做出来有啥稀奇;做不出来就说,喏,他国外回来的也做不成。
“文革”结束后,我开始申请入党,一直不批,有人卡。大概想这个人业务又好,如果成了党员,就是双料人才了,不行。所以一直入不了。
在尿液中发现艾滋病毒抗体
1986年1月,Dr.London到上海来开第一届国际肝癌会议,看了我的实验室说,你再出一次国吧。我考虑了一个星期,跟院长也商量了,决定再出去,一是可以再充实一下自己,二是为医院再争取一些经费,把实验室扩大起来。当时肝炎五项指标测定用的都是国产试剂,结果不稳定艾滋病治愈,我带回的试剂是进口的,非常昂贵,后来就买不起了。
正好纽约大学要建一个AIDS实验室,想要一个中国人,勤快的,有研究肝炎背景的。因为那时艾滋病的感染机制都还不清晰,只知道跟肝炎的传播途径是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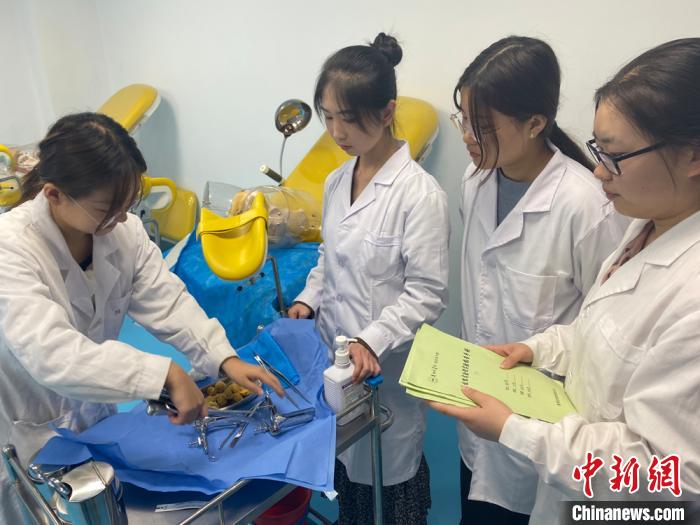
当时,中国一本艾滋病的书都没有。我记得到上海汾阳路医学情报站去查资料,只有第一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摘要,16开薄薄一本小册子。我对AIDS一无所知,本想另等机会,但纽约大学的人通过Dr.London劝我去,我就第二次到了美国,那是1986年7月。
我是新老板第一个招来建设实验室的人。才去2天,他把我送到Buffalo的医疗中心,那里有个实验室,领导者是白血病/艾滋病专家,他那里已经建立起一套HIV的检测方法。老板给我一个月时间,要我把那套实验方法带回来。我学了12天,基本学会了,又呆了8天,要求回去。老板说,为什么?我说,学完了。他说,really?我说,你叫我学的我学会了,你没叫我学的我也学会了。他说,那你回来能做吗?我说,如果不能做,你不要给我工资。他打电话给那边的实验室。血液科专家说,你赶紧让她回去吧,再不走我实验室要让她搬走了。说实话,那些抗体抗原检测很简单的,我两天就学会了,后来就在那里看别的,什么细胞培养啊,全看了一遍,记在本子上了。
回去后我招了第一位技术员,是个意大利小伙子,我们有了一间小实验室,从一个tip order起家,发展到有五六个人,后来跟ABBOTT公司合作,做500例艾滋病毒抗原检测。以后又与CHIRAN公司合作检测艾滋病毒感染者体内的病毒含量。由于这段渊源�熣庑┕�司对我回国以后筹建实验室给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986年12月,一位儿科教授拿了瓶艾滋病小患者的尿让我测艾滋病毒抗原。以前有报道说在艾滋病病人的脑脊液、母乳、眼泪里发现艾滋病毒抗体,但是还没有人做过病人的尿液,我做完抗原检测就想,干脆把抗体检测也做一下,结果是阳性。当时我很吃惊,心想,会不会是一个偶然的特例呢?赶快扩展试验范围,结果在20多个成年HIV-1型感染者的尿里都查到了抗体。
通过尿液检测HIV抗体的新方法令国际医学界为之轰动,1989年获得了包括美国在内共17个国家的医学专利。它的价值在于,较之原有血样检测,验尿更为方便、经济,且是非创伤性的,同时准确率可达97%以上。
那时我已理应回到Dr.London的实验室去,但这个基金会的主席一定叫我留下。我把具体情况跟London说了,他赶来纽约跟我新老板谈了2个小时,最后讲:“我把最好的人给你了,你要对她好。”又对我讲:“医学上一个新发现不容易,有时候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不要轻易放弃。”艾滋病当时还是全新的领域,我对新东西也挺感兴趣,就留下了,转向做艾滋病的研究。
“没有你我们的工作会不同”
我从1986年开始和艾滋病打交道�� 先是在美国实验室认识艾滋病毒,接着到患者身上去收集艾滋病毒�熝芯堪�滋病毒为什么会、又怎样使人发病﹖这些对我来讲绝对是个挑战。说实话,科学界的知识更新非常快,我不笨,记忆力很好,但比起大多数聪明人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我起点也不高,英文不好,没有分子生物学基础,没读过博士,能走到今天,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勤奋。我属于那种认定目标就坚定地走下去的人,而且要走到别人前面,不怕付出。在美国那些年,几乎没有过星期天,不停地学,不停地做,心里可能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文革”耽误的那些年补回来。后来回国在北京那几年也一样,没去过颐和园,没看过一场电影。衣服也不会买,以前是我妈买,后来是先生帮我买。我最要好的朋友是三样:飞机、旅馆,还有艾滋病朋友。
我是1989年认识何大一的。那时正是他研究的黄金期(1981-1996),他扎扎实实做了很多研究,包括在精液中发现HIV抗体。
那时候,纽约市有一个有钱老太太Ms.Diamond。她先生是一个移民,19岁刚去美国时据说身上只有一美元,后来做房地产起家。Ms.Diamond继承遗产后就成立了戴蒙德基金会,一块是提供给搞艺术的,还有一大块就是提供给医学研究和医院建设。1990年,他们想在纽约建立一个艾滋病研究中心,面试了100多个科学家,最后选了37岁、娃娃脸的华人何大一。

1990年10月15日,我来到了纽约医学中心对街的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参加实验室筹建,做何大一的助手。半年后的1991年4月16日,中心正式成立了。
在那里,我完成了我的历史任务:参加了何大一教授主导的全部研究课题,包括1992年开始的鸡尾酒疗法的长期试验。纽约很多著名的感染者都是那里的常客,像打篮球的魔术师约翰逊8年的病毒标本都在我手上。
那时候也想过是不是去读个PH.D(博士),何大一说,你M.D完全够了。他叫我“特快专递(express)”,因为我做起事来动作很快,有时他改主意都来不及,因为我已经动手了,手下的年轻人也常说跟不上我的节奏。越是做得多,越觉得知识不够,越是要拼命学,拼命做,好像这样一天才没白过。我的命很好,遇到了很多好人,他们教我帮我,我也努力,机遇来时就能抓住。艾滋病研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业,科学家的努力可以救全世界很多很多人。
我怎么入的美国籍呢?其实1989年我就拿到了永久居留证,但是1995年有一次去台湾开会,台湾方面刁难我,那边的说,你如果是美国护照�熚衣砩吓�。我一气之下就入了美国籍。飞来飞去确实方便了,但这下好了,现在回中国要签证了。我从小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根深蒂固,改不了的,谁把我当外国人,我心里说不出的别扭。
1993年鸡尾酒疗法出来了。这是许多科学家共同研究的成果,何大一是主要的倡导者。那年我陪他来中国,第一个引荐的人是曾毅院士。1996年何大一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卫生部发出邀请,1997年我陪何大一又一次回来,是前卫生部长陈敏章接待的,他当时就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越来越多了。那时候我就想回来了。
每一个出国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会有一种漂泊感,这时候的爱国心就会非常强烈。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从小渗透到血液里的情感,祖国培养了我,祖国有我的亲人我的师长我的同胞,我应该为她做点事。
1998年7月17日,做了半年准备之后,我带了29箱实验器材和资料飞回来,受聘担任中国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临床病毒学研究室主任。有两点我永远记得何大一的恩:他当时给了最大的支持,把那些大药厂的关系介绍给我,试剂、吸管、培养基,要什么拿什么。还有一次是,我刚回国,我丈夫郑医生在美国心脏病发了,那天正好要跟默克公司谈判,不能回去,是何大一陪他去医院装的冠状动脉支架。所以我在退休前夕给他的信里说: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做,将一如既往�熅⌒木×Α�
何大一在回信中说:Our work would not be the same without you. While we hope you will enjoy the time with your family�� do not be surprised if we call upon you for help and counsel. We still need you. With deep appreciation for your years of contribution to ADARC and China's AIDS effort. (没有你,我们的工作会不同。希望你能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但别惊讶我们可能还会找你商量或帮忙,我们仍然需要你。感谢你多年来对戴蒙德研究中心和对中国艾滋病事业的贡献。)
最自豪的是培养了一支队伍
1990年在美国买了房,每月要付贷款1800美元。1998年回国,在美国没有工资拿了,很快就把房子卖了,因为供不起。

我回来不为挣钱,不想当官,也不求名,所以谁的马屁我都不拍。在中国要做事情是很难的,各种情况都会碰到,有时也看不惯。但下面病人是很苦的,跑下去一看你就想要深入去做。当年预防医学科学院的老院长陈春明教授跟我讲过的一句话:“你只要想是为谁做,为老百姓做,什么怨言都没有了。”这话对我一直有用。
而且我后面还有许多在艾滋病领域工作的海外华人专家,他们也希望为祖国做事情,我算是牵根线吧。
回国的曹韵贞依然在跟时间赛跑。仅仅两个月,就与北京地坛医院合作建立了艾滋病门诊,开始接诊。而她常常买两个花卷馒头放在办公室里,早上一个,中午一个,因为“正经吃饭太费时间”。
过这样的生活,我不觉得亏欠了自己,只是觉得亏欠家人很多。我愧对母亲,她28岁守寡拉扯我们长大,很大岁数了还要帮我操持家务。她病倒了,我在家只守了几天就又得出去讲课,后来她因为医疗事故意外去世,我自己还是医生!我觉得这个内疚是一生都没办法弥补的。我先生在美国做完心脏手术到北京,结果又变成他在照顾我。
小外孙Jake出生时我人在内地,只听说他不会吸奶,三个月大、五个月大时见了两次,发现一些症状,但接触时间太少,我想大概是发育迟缓,直到八个月时再见,他还不会坐、爬,我才警觉有脑瘫的可能,一查果然是。我女儿为了不遗弃这个孩子,放弃了国际贸易极为热门的工作,为他的治疗费尽心血。女儿需要我,可我为了艾滋病人长年在中国各地跑,没有办法帮她。
人到中年,本该是上对父母尽孝,下对儿女尽责,可一直是全家人为我服务,为我的工作服务。我现在很怕一个人开车,会不知不觉想到家里人,会想得出了神。
为谈一个合作项目,她跑了7趟云南,2002年在云南省启动的治疗项目为300例感染者提供了3年规范治疗。8年来,她去了N次河南、山西,足迹遍布所有的重灾区,她负责的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供的CIPRA项目,对山西省闻喜县700例HIV感染者进行了规范治疗。为了打进新疆,她去了不下10次,从一开始只欢迎讲课到后来能去病人家里探视,最终以一片诚意说服了当地政府,治疗得以全面展开,比尔·盖茨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也由她牵线进入新疆。
艾滋病治疗领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曹韵贞说,就是要迅速提高与艾滋病人打交道最多的村医的水平,提高病人的依从性。“都在叫要新药,其实新药来了不好好吃,出现副作用医生不懂得解释说服,动不动就停药,还是会产生耐药性。”
在河南郑州,她自己坐门诊看病人,带徒弟,这些医生又到更基层的医院去讲课,带更多的徒弟。她直绷绷地说:“没有一个省的领头医生不是我培养的,最自豪的就是培养了一支队伍。”她尽力给徒弟们创造深造的机会: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传染科的孙永涛经她介绍到美国免疫学家Broose Walker手下进修,他英语好,最后能在美国坐门诊看病人,回国后带回61万美元的基金项目,建立了实验室,成为中国目前唯一做CTL(细胞毒T淋巴细胞)测定的人;郑州六院的何云也在她的推荐下赴美进修;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周曾权、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张跃新主任都已能独挡一面。
科学事业是不能有半点虚假的,更需要一代一代的接班人。学术界有一些风气不好,就是垄断,什么都要把在自己手上,我就看不惯这种现象。尖端有两种,一种是宝塔形,一种是梯形,宝塔尖上是很突出、荣耀也大,但倒起来也快;梯形上面虽然站了一排人,但很稳固。一个人不是万能的,不可能面面俱到,不是强项也攥在手里……要做老大,要靠自己一点点做出来。不过现在有些领导就喜欢敢说大话的人,做不到也无所谓。
中国一些地方的艾滋病治疗现在政治味越来越浓:为艾滋病人着想的少,对政绩工程、国际形象感兴趣的多。我这样说也许会得罪人,不讲么,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我能做的,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能做了,该激流勇退了。我不想当英雄,离开时就希望听一句话:曹韵贞为中国做了些事情。没有,也没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