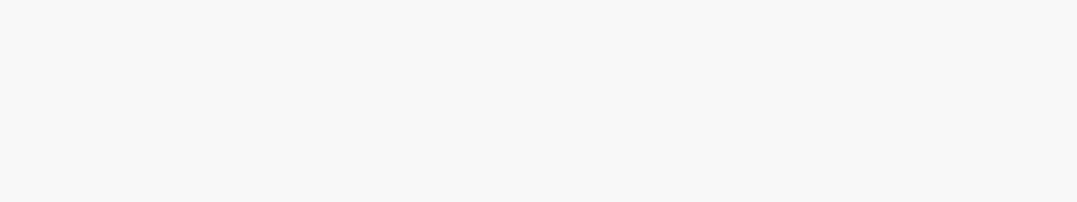

徐风和王淼,均在不到30岁的年纪,感染HIV。在最初的恐惧、焦灼过去后,他们在亲友、医生和病友的帮助下,靠着科学用药,稳定住病情,重建生活秩序,开始学习与HIV相伴一生。

不到30,恐惧死神将至
确诊感染HIV病毒后,徐风决定放弃治疗,离家出走。
2004年冬天,他在北京市疾控中心参加了一次免费自愿检测,当晚接到大夫的电话,“检测结果不太好,你过来一趟吧”。
徐风觉得“好像天塌了一般”。这年,徐风不到30岁,一直在北京建筑工地工作。坐车去往疾控中心时,他一路晕眩:世界看上去新鲜美好,而他得了“不治之症”。他害怕、内疚,想起在老家生活的妻子和儿子。他不确定妻子是否被传染上?孩子呢?
坐在疾控中心的诊室里,大夫宽慰和嘱咐了他1个多小时。徐风一句未听进去艾滋病自述,难以面对家人,徐风决定:不治了,找个地方,自生自灭。

徐风打听到一座寺庙招弟子,便不告而别,手机也关了机。在庙里打坐、念经的日子里,他很想家,两个半月后,鼓足勇气开机,弟弟妹妹的电话接连打进来,由于他无故失踪,母亲忧虑成疾。徐风在电话里痛哭流涕,说自己得了治不好的病。家人劝他回来,一起想办法,放不下病倒的母亲,徐风决定回去,积极治疗,面对一切。
2021年春天,大学生王淼听朋友提起,身边有人感染HIV后的症状。他心中“咯噔”一下,莫名其妙的恶心、腹泻、食欲不振,和几个月前困扰自己的“肠炎”太像了。王淼网购了试纸自测,显示两道杠时,他认为是测错了。再测,还是两条杠。
那一周,他寝食难安,总是忍不住上网检索艾滋病的症状、患者寿命,那些惊悚的新闻或图片,让王淼坠入更深的恐惧中。
他设法联系了同城一位艾滋志愿者,志愿者陪着他在办公室检测,仍旧是阳性。志愿者告诉他,现在HIV感染者按时吃药,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当时的王淼难以相信,坐定在那儿,“眼泪哗哗流了几个小时”。
他是个高大腼腆的北方男孩,临近毕业,他计划着离开老家,去温暖的南方城市闯荡。感染HIV,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和未来的可能性都被关闭了。和徐风一样,他最担心的是父母。他是独生子,“将来父母老了,我先走了。他们怎么办?”
截至2021年10月底,全国报告现存HIV感染者114万例,感染者仍然以青壮年为主。随着抗病毒治疗的广泛普及,艾滋病已成为可防可治的慢性病。但由于缺乏科学的预防、治疗知识,加之感染后萌生的强烈病耻感,许多感染者在确诊后,仍旧极易自暴自弃。
被疾病折磨的王淼去HIV相关的贴吧发帖,“不想活了”。帖子下涌入很多评论,一位母亲发来大段私信,她鼓励王淼,自述自己的孩子也感染了HIV,虽然过程艰难,但她现在也已经接受了。
这暂时止住了王淼轻生的念头。但他仍旧不知如何面对成为HIV感染者的事实,尽管知道艾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血液和母婴传播,日常接触不会被传染,但他还是忍不住担心会传染给别人,在寝室和家中藏好自己的毛巾和洗浴用品。抑郁的他主动断联了所有朋友,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被秘密压得喘不过气,他忍不住,约着最好的朋友去吃烧烤。
在烧烤摊上,他坦白说自己得了病,朋友表情凝重,挨个儿去猜。他说出艾滋,本以为对方会歧视他,意料之外地,朋友和他一起抱头痛哭。

一面共存,一面保守秘密
有了亲友、病友的支持,徐风和王淼开始学习,和艾滋病这一慢性病共存。
徐风回到北京的出租屋,他的母亲、妻子带着儿子都在。他先让妻子和孩子去检查,万幸,他们未感染。徐风舒了口气。
妻子未同意徐风离婚的提议,也再未追问过他患病的细节。两人都是70后,“我们同辈人离婚的很少。也是为了孩子。”或许是怕刺激徐风,家人在他面前从未提过他生病,也未说过重话。
自此,徐风开始走上治疗的漫漫旅程。
随着抗病毒治疗的广泛普及,艾滋病现在已经成为可防可治的慢性病。发现感染后,应尽早接受科学的药物治疗和干预。艾滋病的治疗是持续终身的过程,治疗效果好的话, HIV感染者能获得几乎和常人无异的生命长度和生活质量。
2005年,徐风准备服药时,国内可选择的药并不多,高昂的药价,对于徐风的家庭也是一笔负担。徐风遇上一位“医生”,自称在寻找免费试药人,他给了徐风一瓶胶囊,“胶囊一头白一头黄,一瓶100粒。”服用“胶囊”一个多月后艾滋病自述,好奇药物成分,徐风拆开胶囊,竟发现一根头发,这让他觉得恶心。他去质问,对方才说,药是自己的配方,家人磨碎了原材料后,组装成的胶囊。
这些不明成分的自制药,给徐风的免疫系统埋下炸弹。两个月后,徐风再次去体检,“身体里CD4+T细胞从400多减少到30多,病毒载量超过10万(copies/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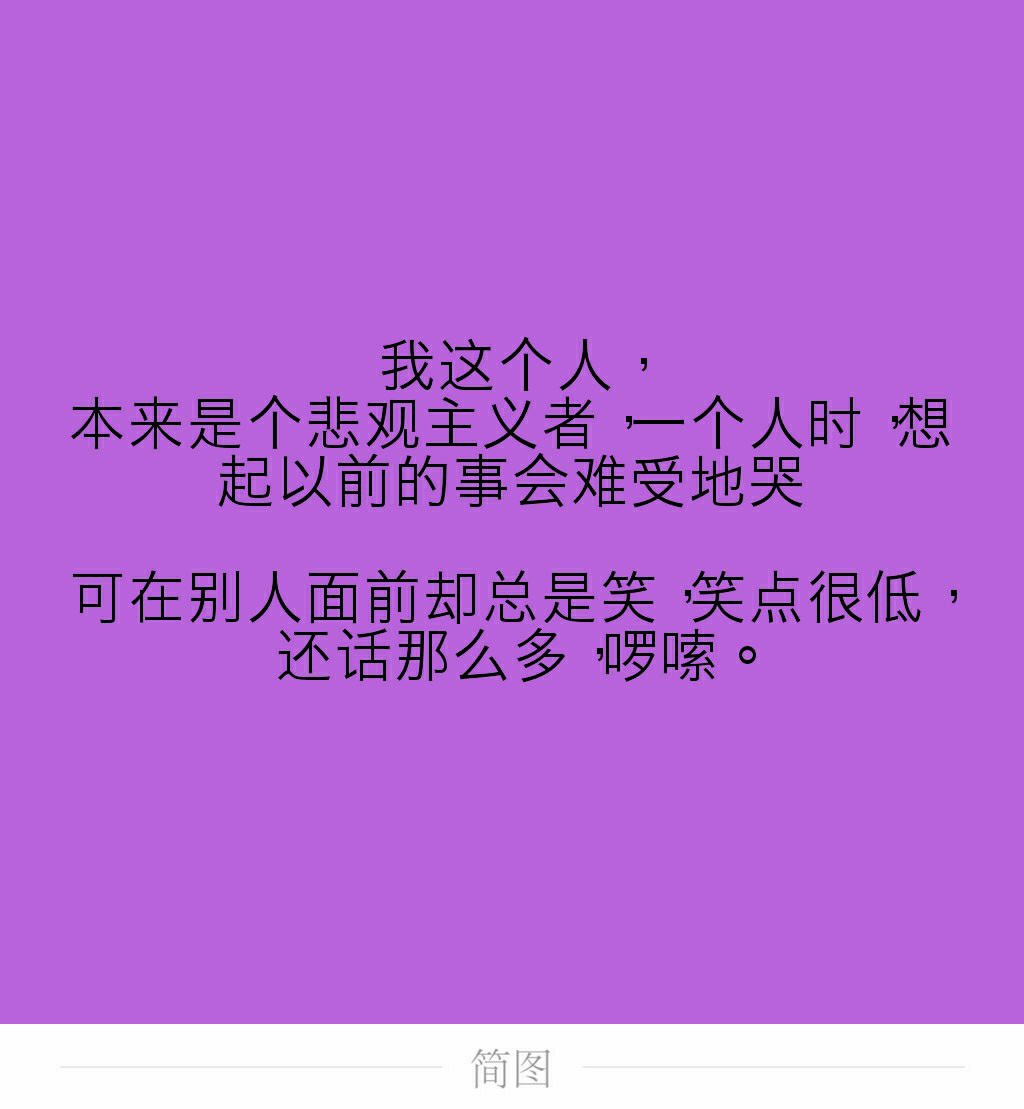
这意味着 HIV病毒正在全面侵袭他的免疫系统。徐风吓坏了,那些天,他总觉得自己身体在发烧。但拿体温计测,体温却无任何异常。
给徐风检查的疾控医生将他转到地坛医院,徐风开始使用“鸡尾酒疗法”,同时服用三种抗病毒药物,抑制病毒的继续复制,帮助修复被破坏的免疫系统。那时候,他一天两次,吃600mg药物,服用的药物多少有些副作用,和徐风服同类药物的病友们会做噩梦。徐风还好,没做过噩梦,但服药后,他的血脂比正常范围值略高些,需要服用降血脂的药物。
好在规范用药一段时间后,他重新体检,身体指标逐渐恢复正常。
生病后,无法再做重体力活,同时也恐惧病情暴露而遭遇歧视,徐风辞去工作。病友和志愿者们构筑的小圈子,成了徐风可以放松待着的地方。当时,每逢周末,志愿者们会组织艾滋病知识科普活动,邀请医生护士为他们讲艾滋病治疗、家庭消毒的知识,最多时,100多位病友聚在一起,白天听完讲座,晚上大家一起聚餐、谈天,徐风总是沉默地坐在角落里。
志愿者冀东注意到总是郁郁不乐的徐风。冀东向徐风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冀东小徐风几岁,2000年前后,冀东确诊时,身体里CD4+T细胞只剩10多个,全身乏力,到了需要住院治疗的地步。当时,国内治疗艾滋病的药很少,他只能拜托别人从国外带来人家不吃的过期药给自己吃,“有什么吃什么,有一顿吃一顿。吃到后来,对许多药都有了耐药性”。
幸运的是,冀东遇上了适合他自己的抗病毒药物,服用后,身体才恢复过来。冀东的坎坷经历与乐观心态,打动了徐风,“如果别人都可以乐观地活着,那我为什么不可以?”
对于HIV感染者来说,从一个团体中获得完全的支持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学会在阳光之下隐藏自己的秘密。
根据中国《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成年人的HIV检测结果只会告知本人,不会通知家人或单位。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身份信息。
他们仍小心地对家人和多数朋友隐藏着秘密,社会对HIV感染者的歧视和污名、对于艾滋病的传播方式的误解仍广泛存在,比如认为艾滋病会通过空气或唾沫传播。两人不止一次听说过,病友在医院被拒诊的经历。王淼的一位病友,妻子做护士的,也不愿同丈夫一同用餐。

生病改变了王淼的人生规划,忧心艾滋病患者在求职、就业中可能遭受的歧视,毕业后,王淼进入了家乡国企工作,他想要离父母近一些。
他也接受了治疗。还是学生时,没什么钱,他服用免费药。为避免免费药可能出现的副作用,他特意忌口了半个月,选择在周五开始吃药,第二天周末能够休息。但当晚吃完药,他还是犯迷糊,发热,身体发软,但服用一段时间后,他觉得不适感轻微多了。
王淼最感激的是自己的主治大夫,她是一位和善、耐心的大姐。每三个月复诊一次。他每次都要全副武装,戴好帽子和口罩,但每次一推开大夫的门,大夫问候他:“小王你来啦。”唠家常般,问问他的近况,告诉他身体各项指标一切都好,王淼就觉得自己的信心又增多一分。
艾滋病贴吧是他的自留地。最煎熬的那段时间,吧友们给了他不少鼓励。现在,空闲时,王淼也会为那些求医问药的网友解惑,拿自己的经历,安慰新确诊、处在绝望中的网友:“按时服药,不自行断药,你看我现在蹦蹦哒哒的,啥事都没有。别放弃,活着不好吗?对吧?”

回归正常生活
如今,王淼的生活步入常轨。国企的工作并不繁重,不忙时,他每两天去一次健身房,一待就是 2、3个小时,确诊后不久,他开始健身,想要提高免疫力。健身小有成效,他说自己一年多没有感冒了,“我觉得我现在比健康的人还健康”。
治疗艾滋病的创新药物也在更新迭代,一天一片、体积更小、服药更简便、副作用更小的复方单片制剂成为HIV治疗新趋势,也让HIV患者回归健康生活成为可能。2021年11月,可一天服用一片、拥有更强病毒抑制率、安全性更高的比克恩丙诺片纳入医保。王淼参加工作后,有了医保,听大夫的建议,他把服用的免费药换成了比克恩丙诺,医保报销后,仅需自付几百元。换药后,他确实感受到,并未有之前服用其他药的不适感,且一天吃一次,也更方便。
王淼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不像从前那样和他们顶嘴了,发了工资,会给父母买礼物。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他喜欢旅游、K歌。王淼喜欢现在的生活,生病是无法更改的事实,但你仍可以选择如何活着。“我现在只想好好活着,比任何人活得都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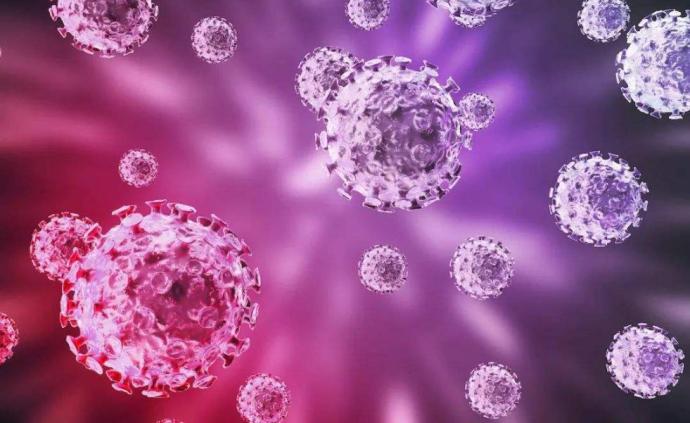
服药后身体稳定的6、7年间,徐风最多的时间,是待在地坛医院或者附近的一栋公寓楼中,这是许多病友心中家一般的地方。从外地来北京看病的病友无处落脚的,可以暂住在那里。二十多年来,徐风目睹了许许多多艾滋病病友的悲欢离合。
他见证一对大学生情侣,阴性的那位不介意爱人是阳性,由于防护不够,阴性的最后也感染,但后来,两人因为未来规划不一致,还是分开了。
徐风能理解,爱、激情是人之常情,但重要的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有性生活的话,一定要有保护。阳性病友要自律。阴性病友要加强防护。使用避孕套,不仅防HIV病毒,也可以防HPV等性传播疾病。”
他也见证了科技发展给艾滋病患者群体的生活带来的改善。徐风印象深刻的一对夫妻,丈夫是阳性患者,妻子在怀孕期间吃阻断药,自然受孕后,来北京定期检查了几次,孩子都是阴性,后来产下一个健康的男婴。去年,徐风在朋友圈里看到,男孩已经读小学四年级了。
而感染HIV的第七年,徐风重新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一直做到现在。他每天按时服药迄今未觉得身体有什么大的异常,但担心目前治疗药物产生耐药性,医生说,可以尝试调整治疗方案。徐风也准备换成日服单片的创新药,方便,也更能保护隐私。他期待着技术进一步发展,有一天艾滋病能够彻底被治愈。
徐风和妻子仍一起生活着,像那些相伴到老的普通夫妻那样,他觉得,“两人的感情已经蜕变成亲情,是家人。”儿子成了家,今年,他的孙子也出生了。十多年过去,他可以通过亲身经历,告诉那些年轻的不安的艾滋病患者,我们能像普通人一样,拥有幸福的生活。
*为保护隐私,当事人均为化名
- END -
撰文 | 周 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