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日,是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
距离1981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5例艾滋病病人的病例报告,已经过去39年。距离1985年中国第一次发现艾滋病病例,已经过去35年。
在这过去的近40年间,艾滋病从一种病因不明的不治之症,到逐渐出现治愈的曙光。目前,全球已有两位患者“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得到痊愈。另一位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的“圣保罗病人”也处于观察之中,即将迎来康复。
尽管治愈的患者只是极少数,但随着艾滋病医疗诊治水平的发展,大部分的患者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并坚持服药,生存时间便可以接近预期寿命。与此同时,艾滋病母婴阻断的技术也已经相对成熟。据统计,95%—97%的艾滋病毒阳性母亲经过规范干预,即可成功实现阻断,分娩出健康的宝宝。
但是对于艾滋病患者的社会关注却远不如医学进步来得迅速。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看来,迄今为止,艾滋病防治的关注点依然是如何让人活,而不是如何活得好。
据中国疾控中心、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联合评估结果,截至2018年底,我国估计存活艾滋病感染者约125万。这125万个带着HIV病毒的身体,该如何参与我们的生活与社会?除了检测、用药、依从性、耐药性、就医机会这些对于他们“患者身份”的关注,身体形象的改变与管理、家庭生活的构建与维系、性与亲密关系也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除了不哭,还应有笑声。这种想象是奢侈的,也是必要的。”黄盈盈在《艾滋病与生活逻辑》一书的导论中这样写道。正如书名所提示的,在这本书中,她尝试关注艾滋病患者的“生活逻辑”,他们是怎样谈性说爱的?他们是怎样构建家庭的?要怎么面对自己日益发胖的身体,怎么开口告诉伴侣自己的病情,怎么决定冒着风险带病生下孩子,怎么让父母接受自己随时可能离世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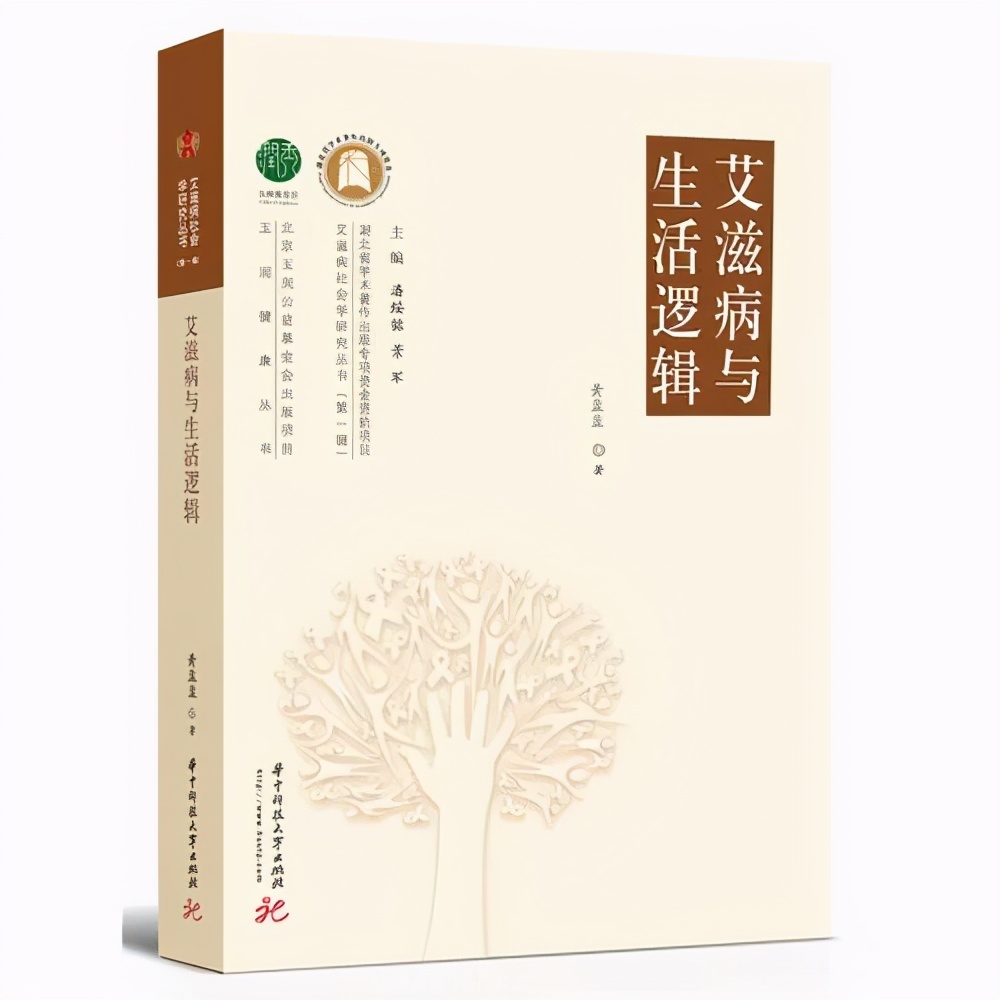
《艾滋病与生活逻辑》,黄盈盈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
原文作者|黄盈盈
整合撰文 | 肖舒妍
01木木的故事 “我已经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爱美了,或者那么自信了。”

由同名漫画集改编的法国电影《蓝色小药丸》(2014)。
木木是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女孩。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开展这个研究之前,在一次卡拉OK聚会上,唱到一半的时候,进来一个充满笑意的姑娘。很爽朗,人影未至,笑声先落。
木木在我们碰到的女性HIV感染者里面是属于非常“都市化”的那类,过去混迹于时尚圈,现在也还经常写点文字。对于木木来说,感染HIV,除了首先体现在对生命的威胁,也意味着个人外表发生了变化。与大多数疾病不同的是,感染这种病毒不仅仅是隐性的、内在感受式的健康问题,也不仅仅是后来发病之后带来的身体上的极大改变,而是在中间用药期间就会在身体层面发生明显的变化。有人会脸色发暗,有人会脂肪转移。对于木木来说,变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体征。
以下是我的学生宋琳和木木的谈话。
/ /
宋:这个病对你身体上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木:我已经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爱美了,或者是那么自信了,至少我现在心理是不那么健康的。为了身体健康根本不顾及形象。
宋:以前很爱打扮吗?
木:你想,以前我穿梭在各种派对里,基本上全都是时尚圈的人,现在都不怎么来往了。以前为了定做一套礼服,会请台湾师傅的那种,现在我买一百块钱的衣服,自己都乐得了。特别是女的,一旦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太有那个心思了,基本上相当于放弃了。
我以前很瘦,得这个病之前腰身从来没有超过一尺九。我现在就留了一条之前的裙子,拿出来连一半都塞不进去了,哈哈,到腿都费劲的那种。
宋:长胖跟这个病有什么关系?
木:有啊,你必须得保证你的营养啊。去年我强制自己减了一下肥,就是运动啊、晚上不吃东西那种,真的减下来了,但是那年身体就特别不好。今年检测身体好了,就是因为我又胖回来了,太有直接关系了。你总要放弃一点儿东西。
/ /
木木的身体情况算是好的了。对她而言,变胖是主要的身体变化。不仅仅是因为要保持营养,也有心理方面的压力,使得身体形象改变很大。木木是属于很招人喜欢的女孩子类型,因此不乏追求者,也有自己心仪的人,但是一旦牵涉婚姻,就因为各种原因自己先行躲开了,其中就包括对自己感染状况的担忧。
/ /
宋:你刚发现这个病的时候有对象吗?
木:没有,刚发现的时候,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是一种心理上、下意识的回避。我会跟别人说,也会跟自己说:我接受这个病了,我还能活多久多久,我身体挺好的……只是我不能结婚了,但是我从始至终也没有觉得结婚是(必需的事情)。所以患病的前三四年,我觉得对自己一点影响都没有,我觉得我精力充沛,我可以帮助别人。反而是时间越久,经历得越多,才发现自己是蛮在意的,其实是比别人更在意,只是不像别人那种能表达出来,能宣泄出来,真正正面地去接受,其实不能,其实做不到……
宋:这个病对你找对象有没有什么影响?
木:当然有影响了。如果不是这个病,我肯定放开了找,我肯定找条件最优秀的。有个国外的公司在中国驻扎的CEO对我特别好,追了我四年世界艾滋病日,我不能答应他。好多条件很好的,而且我特别欣赏的,我都没办法答应他们。
宋:就是觉得不能跟他说这些事情?
木:绝对不能说,因为那是我朋友的同学。而且他是有社会地位的,就算是他接受了,我也不可能和他在一起的。包括有些演员什么的,我不可能跟这些人在一起。这事儿一旦公开了,就是天大的事儿,不光他毁了,他家也毁了。我就得找一个默默无闻的,没有人会在乎的小人物。但你真找那种不名一文的人,你将来真病了,他真养不起你啊,他真伺候不了你啊,很尴尬的。
宋:就一个合适的都没有碰到?
木:可能是我想的太多,这个圈子里毕竟还是有姐们儿结婚的,而且也是跟正常人,但是我要求的可能是(比较多)。没关系,反正我有家人,老了再说吧,我不在乎。就算心里再着急,我也不太想赶紧胡乱抓一个,或者就冒个险。
/ /
木木对于自己的病毒载量与CD4细胞非常清楚,医学的知识也给予了她寻求亲密关系的力量,但是在面对婚姻时,由于涉及了更广范围的人际交往与责任,木木选择的是逃避。在以上这段对话里,有着大多数女孩子对于情感与婚姻的看法,也有着一般家庭对子女婚姻的期待;有木木因为感染了HIV而生发的诸多顾虑,也有木木家人为保护感染的女儿而对她的支持与体谅;有对自己身体的自信以及对于“正常生活”的追求与实践,也有因病而闪现的担心(在婚姻与生育的问题上凸显)。

《蓝色小药丸》,[瑞士]弗雷德里克·佩特斯著,陈帅/易立译,后浪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11月。
02珍珍的故事 “我希望自己能活到女儿20岁的时候。”

寻访艾滋病感染者的纪录片《在一起》(2010)。
珍珍今年28岁,有一个1岁多的孩子。她与老公两个人都是感染者,是在结婚后不久发现的。两个人谁也不知道是怎么感染的,也觉得没有必要深究这个问题。
在珍珍看来,自己算是幸运的,爸妈和婆婆对她都很好,在这里也有不少朋友。最重要的是,在几次打胎之后,珍珍与老公要了一个小孩,对未来也有信心。在访谈的结尾,珍珍说的是“我觉得我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隔阂”。
不过,家里人与朋友对于感染都不知情,珍珍觉得毕竟这个社会对艾滋病充满歧视与成见,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让他们知道的。
谈话是从珍珍正在玩耍的女儿开始的。
/ /
宋:她(孩子)现在一岁了是吧?
珍:嗯,一岁零三个月了……因为早产才这么小个儿嘛,就是个子小,别的什么都很好。
宋:你们当时是特别想要小孩吗?
珍:当然想要了,我跟我老公那时候也是奉子成婚。结了婚多高兴,但后来却把孩子打掉了。
跟我老公结了婚第三天,我老公就被打伤上医院了。在医院体检抽血化验,化验了说有点问题,还没让我老公知道,是先让我知道的……我挺着大肚子一直陪着他,他住的人民医院旁边就是妇幼保健,我就去查,查出来也是阳性。我是等到他出院的时候才把孩子打掉的。
宋:那时候来不及做母婴阻断了吗?
珍:我们那边的小县城哪有那么好的条件,虽然医生也说是有母婴阻断,但是感染率是非常高的,还是建议我打掉。我就想那能怎么办呢?但是他们那儿还不给做(指堕胎)。
宋:他们是做不了还是怎么样?
珍:不是,就因为有这个病,不接这样子的病人,让我们上广州市区专门的医院去做。但是太远了,费用也太高。后来就找了比较小的一个诊所给做了。
本来那时候家里人多高兴,我跟老公是很不容易过来的,我们俩一直都被反对,就因为有了孩子,家里不同意也得同意了,两个人才能在一起,知道我怀孕了都很高兴。突然间说不要孩子了,我们还找了借口。
宋:你怀这个孩子顺利吗?
珍:本来一直都认为不能要孩子,每次家里人问,都烦死了,心理压力很大,我跟我老公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很想跟家里人说我们不要孩子了,但是每次都只能说我们条件不允许啊,家里环境差养不起啊,我们在这边没人带什么的。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别人说有母婴阻断,去领药的时候就问医生。她很热心,说现在90%以上的不会感染,她做了那么多例,都没有感染的。她支持我们要,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当时我们俩一出了医院就高兴地哭了。
宋:你们俩高兴是真的自己很想要孩子?
珍:因为本来就很想要,你不知道我有多难过,每年跟他回家过年,他弟弟都有孩子了嘛,两个孩子都那么高了,他特别喜欢孩子世界艾滋病日,去跟他们玩,我有时候想着会嫉妒,他甚至会冷落我去跟那两个孩子玩,我知道他很喜欢孩子,但是不敢要呀。
听到大夫那样说,我们一出门就抱着哭,人家看着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傻了呢,门诊进进出出那么多人,但是我们也顾不上了。
宋:母婴阻断就只是吃药,还是?
珍:母婴阻断就是我正常地吃药,她出生的时候给她吃药,好像是口服液。
有这个孩子我已经很满足了,虽然说瘦了点,但是我很欣慰。她就是我们的开心果啊,可逗了。每天起来就爬过来亲我脸蛋,叫妈妈妈妈,把我弄醒了。她还抠我眼睛抠我鼻子,小坏坏,会叫妈妈。我还没起呢,就提着鞋子给我。
宋:你有想过小孩以后怎么去培养她吗?
珍:远的也不知道自己身体怎么样,我主要是担心寿命这方面,反正就是好好地过好每一天吧。如果我的寿命很长的话,我会让她活得很好。现在就为了她攒点钱吧,让她有个好的环境吧。我希望自己能活到她20岁的时候,这样就很满足了。我的心态确实是很好的。
宋:有孩子以后你们有什么变化吗?
珍:变化可大了,开心了很多,也有压力了,因为要为了她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她很坚强的,爱哭爱闹爱玩。
宋:你们还挺好的,就觉得你们是不幸中比较幸运的。
珍:我感觉也是幸运的了,还好没死掉,要死了多可惜啊。前段时间不是报道了吗,国外有一例婴儿感染之后治好了,第一例。以前从来没治好过啊,所以报道了之后就很有希望,以后研究出来了,真的可以治了,那多好啊,我们也盼着这天早点到来,我希望我能活到这一天。现在不想这个问题,平时都不想,反正对这个都不是太在乎了,要不然你老想着这个活得多累啊,想它干什么。
/ /
珍珍看着挺能干的,但不张扬,与木木相比,不是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是有股劲儿。她的叙述也是不紧不慢的,比较淡定。在这种缓缓的叙述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得知HIV的震惊心理,打胎、怀孕以及生孩子过程中的痛苦、忐忑与艰难抉择,以及得知孩子没有感染之后的那份欣喜与幸运。
在这个有关孩子的片段里,既有女性因为感染了HIV而带来的特有生育顾虑,也有一般女性的生育经历与想法。珍珍是不幸运的,因为感染了HIV;珍珍又是幸运的,在医学的发展及某位医生的鼓励与支持之下,顺利地生下了女儿,且是阴性。自己与老公的身体也没有太大的异样,包括外形与感受。而珍珍的案例,也给了想要孩子的女性感染者们一线希望,朝着正常人的生活又迈进了一步。

《积极生活手册:HIV与我的生活》,爱白文化教育中心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
03李姐的故事 “我妈看着我哭,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没了。”

讲述艾滋病与人性的电影《最爱》(2011)。
李姐曾总结过圈里人找男人的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是找个圈里的(HIV感染者),这样就不存在谁歧视谁的问题,可问题是,按照李姐的转述,圈里的男的长得太丑了(注:因为长期吃药,药物副作用带来肤色以及形体的改变);第二种可能是找个正常的男的(非感染者),但又担心被发现,就算是男的愿意,还要考虑他的家里人,而且担心以后生活中的磕磕碰碰;第三种可能是找个(男)同性恋,可是也有问题,只能看不能碰。
以下是我和李姐的对话,更多像是向她的请教。
/ /
黄:圈子里单身的多吗?
李:圈子里单身的多,没小孩的也挺多的,目前有婚姻的特别少。也有去相亲的。像一个在疾控做志愿者的小孩碰到有合适的就会给人介绍。有一个人就跟一个同志(男同性恋者)结婚了,因为她特别想要孩子。
黄:是形式婚姻吗?
李:也不算吧。其实同妻特别痛苦的,他们俩睡在一起,脚碰到了都会马上弹开,像单身的反正看不见也不想要,但是跟男同在一起看得到要不了。不是说非要性,但是没有性生活也不行啊。
黄:那找直男呢?
李:也不好找,抛开长相啊、经济条件啊、年龄啊,大多数都已经成家了,合适的人很难找。圈子太小了,普通人找对象还难呢,何况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
黄:那找病友圈外的呢?
李:不知道怎么张口说呀,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有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姑娘前年找了个男朋友,是在咖啡店认识的咖啡店老板,两人特别好,男方的妈妈和小姨都特别喜欢她,催他们结婚,结果把她吓跑了。一来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开不了口,二来是怕说出去万一他们给传出去了怎么办,那她还怎么在那儿生活。就算是这个男的同意了,那他家里人呢?
黄:可不可以不告诉家里其他人呢?也许这个男的会同意啊。
李:不太可能。她跟我说她太痛苦了,有四个男的追她,条件特别好她都不敢答应。她又特别想要一个孩子,她说平常上班的时候想不到自己是个病人,但是一谈到结婚的事就特别苦恼……有的人可能现在可以接受,但是以后也还是可能会嫌弃啊。
有个姑娘现在就跟她初恋在一起,查出来之后她男朋友天天在医院伺候她,给她做饭洗衣服都行,但就是不碰她,甚至跟她说无性生活一辈子都行,但就是不敢碰她。
黄:戴套也不敢吗?
李:她之前跟他说过,但是他一听就生气了,说你就不拿我的命当回事。其实我们也觉得这个男的已经挺好了,也没有离开她,还照顾她,但是就是过不了这个坎。
黄:像病友之间结婚的还是会好点?
李:像地坛医院的一个女孩,我问她老公对她好不好,她说好是好,就是他长得太丑了。我也会劝她有个伴就要好好珍惜,因为真的太难找了。还有结了婚的,两个人都是感染者,刚生完孩子做的母婴阻断。
/ /
而随后,我们把话题转向李姐自己的生活。虽然也有人介绍,但是李姐并没有积极地去找。刚开始的时候,***妈也不让她找,说:“我养着你,你别找人了,要是传染给人家了,咱们管不管啊?”李姐自己也担心如果双方都生病,会给家里人增加负担。再加上现在吃药人变黑了,也胖了,更不好找对象了。
李姐说:“现在好一些,早期吃的一些药脂肪转移的副作用很大,那时候屁股和腿上都没有脂肪的,一拳头下去就凹进去,别人看见肯定会问你怎么这样了,我也不能跟人家说。现在吃的药好多了,就是吃后有色素沉淀。早些年我都不愿意出门,觉得别人一看就知道我是病人。我都吃了十年药了,现在药的副作用小一些,加上还有组织,心态上就好一些,刚得上那会儿经常哭。”
李姐有一个儿子,现在上初中,挺让人省心的。比较幸运的是,李姐的家里人对她的支持挺大。当然,家里人,即便是最亲近的人,态度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李姐说:“刚开始不好,我之前经常去我姐姐妹妹那儿吃饭,刚查出来的时候她们都吓坏了。我姐姐姐夫一直不敢去查,虽然跟他们说了不会传染。后来他们为了生二胎去查的,查完之后他们特开心地跟我说没有传染上,现在就好多了。”
“转变最大的还是父母,我刚得病的时候他们就担心我活不了多久,我老公发现之后半年就没了,他死的时候才26岁。那会儿我跟我妈看电视,她就看着我哭,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没了。我们那时候一起出去逛街她也不敢拉我,现在好了,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她也牵着我,也陪我试衣服,跟我一起吃饭,我妈妈对我支持挺大的。”
即便是现在,虽然家里人对她很好,李姐自己依然有所顾忌,不愿意给家里人带来更多负担。“不愿意给家里人带来更多负担”,这样的心态在我们与其他女性的讨论与访谈中多次被提及。关于“负担”的具体指向,在每个人那里会略有不同,包括告知家里人后怕家里人担心、怕传给家里人、怕找个病友会增加家里人的经济与照料负担,等等。
李姐、木木、珍珍的故事仅仅是女性HIV感染者其中的一些片段。这一个小小的研究也仅触碰到了开始走出家门,经过HIV这个医学检测结果所带来的死亡威胁阶段,开始慢慢适应携带着HIV生活的女性的一个面向。但是,即便是这冰山一角,也带给我们很多启发与思考。
虽然我知道在医学技术的发展浪潮下,艾滋病正在不断地向着慢性病的方向发展,对于死亡的威胁不比之前(在某些社会中确实如此),怀孕生子也不是问题,但是在社会歧视、医疗歧视、贫困依然严重的当下,死亡威胁(不一定是自身情况,可能是朋友、报道中的人物)与“孩子万一感染”的顾虑时不时会敲打一下这些女性的生活,我们应该如何想象更为常态的生活?常态的生活想象,是否依然过于奢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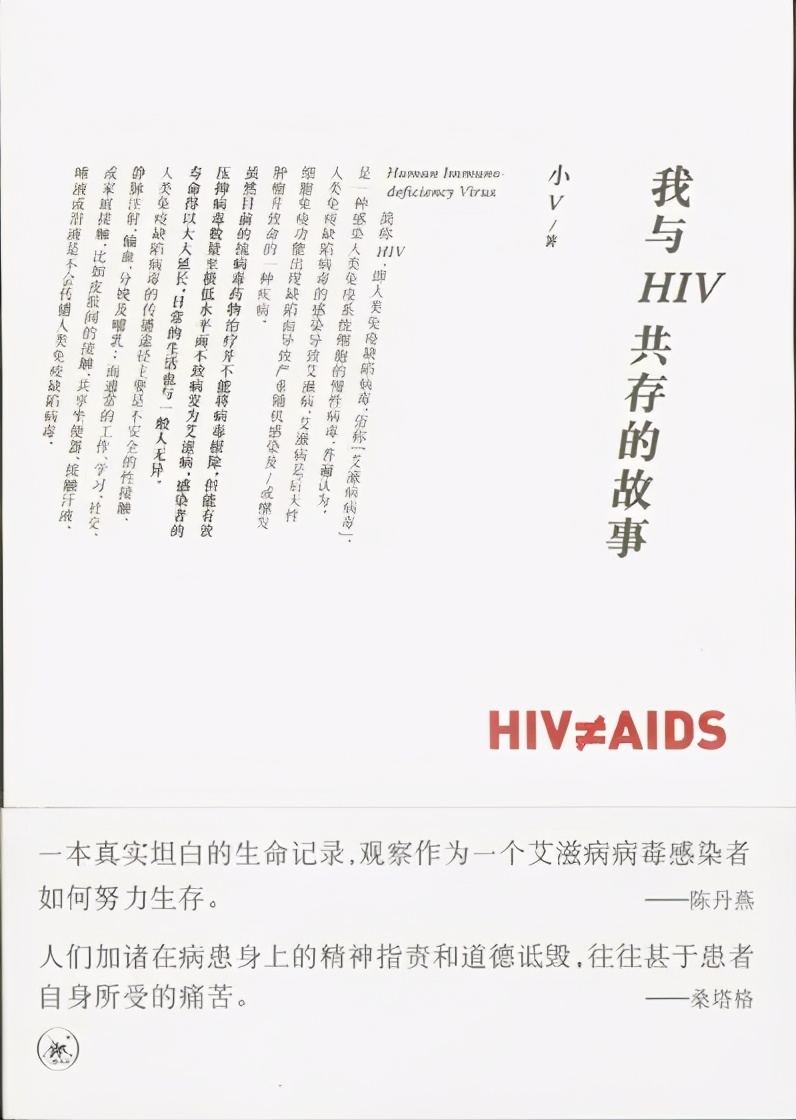
《我与HIV共存的故事》,小V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9月。本书讲述作者与艾滋病病毒共存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