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出门的那一刻,宋益忽然害怕了。
11月16日,朋友约他出来。他答应得很爽快,但见面前一小时,恐惧像从地底蹿出的火箭一样,迅速控制了他。
25岁的宋益是上海一所高校的理科博士生,日常生活就是带着手机、充电宝往返于宿舍、实验室、食堂三点一线。他偶尔会和实验室的同学聚餐,但大部分时候,没有社交。
一年多前,宋益的课题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他一度精神低迷,无心做事,只想睡觉。这期间,他发生了一次无保护的性行为。
之前,他一直很关注艾滋病有关的问题。那次行为之后,他忽然想到感染的概率问题,开始恐慌。“慌了之后就去检测,因为不是很了解就越想去了解。从而陷入一个想去了解更多的循环里面。”
他总觉得随时会暴露在被艾滋病毒感染的风险中,为此,他不断检测,疯狂逼自己啃读资料,电话咨询,看心理医生。但恐惧始终盘踞在他的脑海,从未彻底消散。
不同于人们对艾滋病的暂时恐惧,宋益这样的恐艾群体长期笼罩在巨大心理阴影中,通常伴有焦虑、抑郁、强迫等多种心理症状和行为异常,属于神经症谱系的“恐艾症”。

马桶上的血
高危行为后,宋益开始习惯天天量体温。一直很正常,他的焦虑感有所减轻。结果因为与人发生肢体冲突,又被人咬了一口。没有出血,但恐惧感又升了起来。
恰好在那段时间,他看到南京一位HIV病毒携带者咬伤法官的新闻,受到刺激。两星期后,又开始腹泻、发高烧。这一系列事件逐步加剧他的恐惧。
后据央视网报道,南京被咬伤的法官,经过健康检查无碍,也未感染艾滋病毒。而宋益去医院检查,发现自己只是细菌感染的急性肠胃炎发作。
那天出门前,他想到的就是这些过往经历。一开始,他拒绝了,后来,又调整了心情,才终于出门。一路上,他都戴着耳机听轻音乐,这是他调整心情的一种方式。
约宋益出来的人叫小T,她是上海一家健康管理咨询公司医学部负责人,日常运营一个名为“H-Shield艾滋病预防”的微博账号。宋益就是因为恐艾的问题,和小T认识的。
每天小T都会在微博私信上收到几百条千奇百怪的问题,大都和担心自己感染艾滋病有关。诸如,“买的二手钢笔会不会有机关?”“走在路上被外国人撞到,他会不会趁机扎针让我感染?”“买的奶茶会不会有人加艾滋病血液?”
有些私信问题脑洞太大,小T专门创建了“全世界都要害我”的话题,收集微博私信中网友的奇葩疑问。
这些疑问,宋益也有过。
宋益的宿舍卫生间为公用,一次上完厕所,他不经意看见坐便器上有血迹。他担心这是有人故意留下血迹,要感染自己。为了测试是否如此,宋益强迫症发作,做了一个实验。
他揪下自己几根头发,放在马桶内壁不起眼的地方,观察了两个星期。这期间,他发现头发还是在那里。“通常大家都在用蹲厕,马桶根本就没有人在用,就感觉真的是在自己吓自己。”宋益说,纵然如此,他心里还是不安,尽量不回寝室睡觉,不去那个卫生间。
“你写这个肯定会有人说是自己作的,让他们去说吧,人这一辈子犯点错也纯属正常。”宋益说。
“祝大家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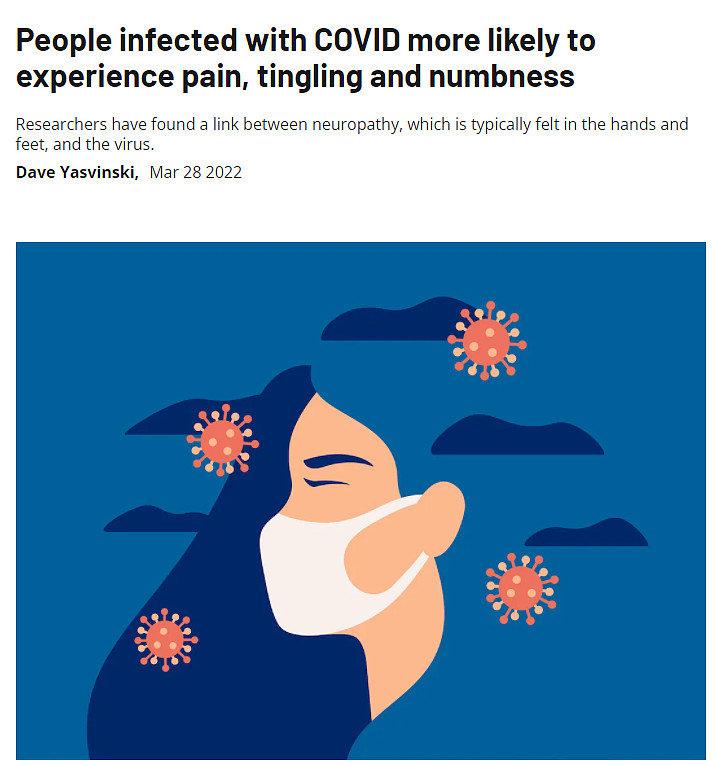
感觉需要帮助的时候,宋益会去百度的恐艾吧。他最早认识小T,就是在恐艾吧里。当时除了在微博与恐艾者互动,小T也常出没于各种贴吧。
恐艾贴吧是恐艾者的活跃主阵地。截至发稿前,超过11万人关注了这个贴吧,这些人发了1482万个帖子。

贴吧里,满屏诸如“和按摩院的性工作者发生了高危性行为,会被感染吗?”这类问题,大多焦虑也源自无保护性行为、边缘性行为、伤口或黏膜接触潜在风险的血液或体液。
大家称呼彼此为“恐友”,平均每分钟都有帖子刷新。他们拥有内部独特的祝福方式——“祝大家阴”。
阴是指HIV检测结果为阴性,证明没有感染。
据成都市恐艾干预中心咨询师、中科院临床心理学博士研究生张珂估计,全国的恐艾人数总体接近100万人,年龄层次集中在20-30岁,大学生为主。男女比例4:1,其中触发男性恐艾情绪的多为商业性行为,而女性多恐惧生活中的文眉、洗牙之类的感染。
张珂原来从事心理咨询,2009年,恐艾干预中心成立,他开始涉足心理咨询和艾滋病防治的交叉领域,拥有十年恐艾干预经验。据他介绍,每年都有陷入中度、重度抑郁症的“恐友”反复求医,甚至会有轻生心理。
24岁的自由职业者江佑棋也是一名恐艾者,他也因此认识了小T和宋益。据他回忆,自己的恐艾经历来源于一次狂欢派对。
那天晚上,他喝得昏天黑地,凌晨醒来恐艾,他发现自己躺在草坪上,难受得想吐,之前的记忆全部断篇儿。但他怀疑,自己混乱中,有高危性行为发生。
一周后,他胸前和背后开始出现带状疱疹,白天手上脚上不停渍汗,没有胃口吃饭,偶尔轻度发烧。“那时候很恐惧,怕自己过不来,觉得应该是‘艾上了’”。
后来,江佑棋才知道当时是因为情绪恐慌带来的神经紊乱。这种症状和艾滋病感染后急性期症状有类似之处。
“艾滋病感染后的急性期症状并不具有特异性,不能单凭症状判断是否感染艾滋病。”成都恐艾干预中心的郭海燕说,“这也正是恐友们最常焦虑的问题。”
除了对症心理,“高危行为”和“艾滋病检验窗口期”的定义是始终萦绕于恐友头顶的两大迷思。带有此类关键词的问题高频、反复出现在恐艾贴吧、微博私信和QQ群之中:“和艾滋病感染者接吻,牙龈出血了算高危吗?”“高危后四周开始查,查到九个月共12次,可以彻底排除感染了吗?”
今年一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其中对艾滋病窗口期定义进行了更新:“窗口期”时间长短根据不同的检测方法而定,绝大多数一周到三周左右可以基本确定。
而张珂认为大多数恐友还是在遵循一种标准仪式感,选择了自我最认可的窗口期进行检测。就像前述9个月查了12次的网友。
涉足恐艾问题十八年来,成都市恐艾干预中心陈晓宇接触到的大量恐艾案例告诉他,来咨询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感染了艾滋病的,“恐艾的不感染,感染的不恐艾”。
800份检测试纸
马桶事件过后,宋益的恐惧达到了峰值。
他电话咨询了恐艾干预中心的郭海燕。电询中,他将自己的疑问和担忧和盘托出,结果发现自己所获得的专业信息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医生。
“恐艾情绪本质上是焦虑、强迫的一种体现,落实到生活中会将这种恐惧泛化,就是恐日常。”郭海燕解释,“他们很少能够意识到这种焦虑和恐惧来源于自己心理问题,而非对艾滋病知识的缺失和检测的不准确性。”
面询过形形色色的“恐友”,咨询师陈晓宇一般会先看行为,是否符合艾滋病传播的三种途径之一:血液传播、性传播、母婴传播。然后再对行为是否为高危行为进行风险评估,先确定感染源:“首先你要和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有接触,没有感染者,发生什么都不会传染。”
陈晓宇说,其次是否有开放性的伤口,第三要接触到对方具有传染性的血液,是否有体液交换,第四,必须满足一定的量。
宋益当时觉得这是概率问题。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后,他怕自己就是那个“万一的感染者”,他缜密地思考每个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即使做了检测,也有检测不出来的概率。试剂有没有坏?人为操作有没有失误?有没有漏检?都是存在一定概率的。”
即便他很清楚,这种概率比一场交通事故要小得多,担忧已经成了他的一种惯性,几乎从没有体会过轻松的感觉。

2016年7月14日,英国伦敦,哈里王子参观伯勒尔街性健康诊所(Burrell Street Sexual Health Clinic),并接受了抽血检测艾滋病(@视觉中国图)
今年7月,一颗叫OK的近地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这个事件又让宋益开始纠结概率,“人类差点就灭绝了”。
一位志愿者也认识一位高危人群朋友,因为怀疑自己被感染,买了800份检测试纸。
“我们一般都是建议高危人群每三个月查一次。”他说,“但是他一个月就查完了200份。”结果,都是阴性,没有被感染,但他还是不相信,一次次地去试。
“可以当超人”
在成都恐艾干预中心,张珂每天面对面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恐友”,也有电话咨询。在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需要接收面询者累积了数月乃至数年的负面情绪。“做心理咨询是一件极其耗脑,耗精力的事情。有时我实在太累了,稍微闭了下眼睛,咨询者就觉得我没有认真用心。”
长期面对高度敏感的恐艾人群,张珂的疲态清晰可现。稀少的发量,后移的发际线,常年携带的手提皮包四周有开裂痕迹。谈话期间,他有一半时间是在闭着眼睛回答问题,这之前,他刚做完两位恐友的面询。
刚开始,中心为纯公益模式运营,为了维持长期运营,2012年底张珂开始转向付费咨询。
最初80元每小时,现在200~800元每小时不等。据张珂介绍,除了抵扣房租和人员成本的考量,收费在一定程度上让咨询变得更加高效。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接受付费咨询。干预中心时常遇见宁愿花几千、几万去寻求商业性行为,也不愿意出钱咨询的人。
曾有一位咨询者跪在张珂面前说没钱,请求他的帮助,张珂怜悯心起答应帮他免费咨询。但在后来的面谈中发现,对方花五千元找了性工作者。“当时我就哽住了,觉得这个表演人格实在是太强了。”张珂说,目前,中心仍保留提供给持证贫困人员的免费咨询服务。
如果有咨询者来乐山,陈晓宇一般都会亲自去接站,然后安排在离自己家不远的快捷酒店入住,条件允许的话,还会带着恐友去爬爬附近的峨眉山,看看乐山大佛。多数情况下,考虑到时间和金钱的损耗,他并不建议恐友特意跑过来面询。
陈晓宇去年曾接到一个高三学生的咨询电话。对方在路上捡到一个情趣用品,非常好奇,捡回去用了一下,用完在网上一搜索,恐惧和焦虑马上淹没了理智。他觉得自己可能被感染了,拒绝回学校读书,害怕传给班上其他同学。
“这是个非常单纯的孩子,心理上有些轻微洁癖,加上青春期的压抑,学习压力比较大,多重因素导致了情绪的爆发。”陈晓宇在电话这头对其行为进行了风险评估,在排除感染艾滋的可能性后,对他进行了心理疏导。今年夏天,这个孩子和陈晓宇分享了优异的高考成绩。
“恐艾的很多人要保证自己处处都万无一失,学习一定要努力,不能出差错,让自己丢脸。”陈晓宇接触的案例中,很多恐友都对自己有高标准和严要求,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出现任何的风险。
咨询结束,还有人想认陈晓宇做“干爹”,他听到笑了笑:“后宫这么多,他们只是想让我独宠他一个。”现在,陈晓宇在微博上已经累积50万的粉丝。
张珂和陈晓宇还曾打算去峨眉山开设“恐友”疗养院,不过暂时也搁浅了。两人的精力目前完全不够用。
除了恐艾中心的咨询,陈晓宇还在乐山疾控中心全职工作,张珂同时做一些情感咨询填补干预中心入不敷出的情况。之前试着培训过一些恐艾咨询师,想增添人手,但真正坚持下来的人寥寥无几。
周一,由于忙碌,原定于下午五点至六点的恐艾中心QQ群线上答疑,张珂延迟到了晚上七点半。QQ群里有人提问:很久没有去集体宿舍,怀疑放在衣柜里的内裤被人恶意放了血液,会不会得艾滋病?
这些是咨询师不厌其烦回答过的众多问题之一。时间久了,他们发现,几年过去了,有些人还是没有任何改变,永远在不停地找问题,问相似的问题。
难得的机会,这是咨询师们可以发挥幽默的问题,张珂皮了一下:“老师觉得你(把内裤)穿(在外面)可以当超人。”
恐惧的无底洞
宋益和小T、江佑棋坐在上海世博公园咖啡馆外面的座椅上,背后的露天广场持续不断回荡着施工噪音,这令宋益有安全感。室内太过安静,反而会让他恐惧。
面对科研上的压力,他表现出一丝无力,感觉怎么活都是活:“科学这个东西是可以被否定的,它是一个上升的东西,没有什么能给我一个很满意的十全十美的答案。”
事实上,像宋益、江佑棋这样经常相聚的“恐友”并不常见。
“恐友都觉得有恐艾症并非一件光彩的事情,甚至很耻辱,大部分‘恐友’都将自己捆绑到道德的最低点上。”张珂说,即便是线上的恐友,离开网络,他们也很少在现实生活中抱团取暖。
之前,宋益打电话到成都恐艾中心进行咨询,咨询师郭海燕给他的建议是:马上停止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远离信息持续的刺激。第二,找医院用药物干预治疗。第三,多运动。

除了实在不想运动,前两条宋益都做到了。
他去心理门诊,寻求药物治疗。心理门诊医生给宋益开了舍曲林,一种治疗抑郁、强迫、恐慌的处方药,副作用是头晕。两个星期后,父母担心副作用太大,帮宋益把药给停了。
恐惧在他心里从未消散。晚上睡前他会想着给自己写个墓志铭,但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没有钱买墓碑。好在,他的失眠有所好转。
自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在美国被发现以来,国内媒体对艾滋病的宣传普遍施行恐吓策略。一方面将艾滋病塑造成“致命杀手”,渲染其不可治愈性和致死性,一方面将其与“堕落”“滥交”等不道德的性暗示标签捆绑。
随着鸡尾酒疗法的普及,艾滋病的死亡率至今已大大下降,感染者的预期寿命也可接近正常人。但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偏见已深嵌入社会群体的潜意识中。
“社会的偏见将‘恐友’们的焦虑赋予了一种不道德感,同时又和死亡挂钩,这在短时间内对人的心理冲击是非常之大的。”张珂说道。
2018年4月,中国第九起艾滋就业歧视案,感染者第一次获得胜利,用人单位主动接受艾滋病感染者回到单位,但据《GQ》报道,胜诉后感染者和用人单位签订的是一份独特的“远程合同”,感染者在官司胜利后再没有回到过单位。
在“恐艾”这个群体潜水久了,宋益逐渐发现恐惧就像一个无底洞。
“有时候,恐惧到一定程度,我就想看一看恐艾吧,想从里面找一点点希望恐艾,但往往越看越被人带节奏。”宋益说,很多人对艾滋病的恐惧集中在那里,反而加深了自己的恐惧。“因为恐惧这个东西是会蔓延的。”
(文中小T、宋益、江佑棋均为化名)



